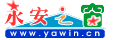
身家百万“笋老大”:有钱大家赚,你富我发大家发
想起因为贫穷而失学的妹妹,林维福发誓要挖掉穷根
1966年1月21日,林维福出在福建省永安市贡川镇龙大村一个普通农民的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个普通农民,靠着一双勤劳的手艰难地养活着一家10口人。在6个兄弟姐妹中,林维福是老三,因为贫穷,17岁那年,数理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林维福初中刚毕业便缀学务农了。但这对于林家6个兄弟姐妹来说,林维福已是最幸运的一个了,因为他是家里唯一一个读到初中毕业的孩子。
1984年12月,贡川镇成立了木材公司,镇里招聘木材购销业务员,为脑瓜好使,林维福幸运地被聘用了。
上班的头一个月他领到了60元工资,虽然比乡政府的正式职工少了一半,可他还是高兴过一阵子,因为这已经比在家务农强多了。
参加工作后,他参加了北京成人教育学院组织的市场营销专业函授。由于精力充沛、业务精通,林维福是镇木材公司的业务骨干,只要有出差外地搞木材销售的机会总少不了的林维福。
1990年9月18日,林维福向镇材公司递交了辞职申请,这很让原本对林维福的印象一直很好的镇木材公司的领导感到意外,因为历来都只有千方百计留下来的临时工,而没有象林维福这样主动提出辞职的临时工,尽管领导们一再挽留,可林维福去意已决,也只好同意了他的请求。林维福之所以要坚决辞去镇木材公司业务员的工作,还是因为家庭贫穷。几年来,做为镇木材公司的骨干业务员,林维福干的活没有比别人少,可工资永远只是正式职工的一半,更让他感到前途渺茫的是,象他这样不占国家人事编制的临时工,年纪稍大一点就得被辞退。想起曾经考上永安市重点中学,却因为贫穷而失学的小妹,再想想那每月只有100多元的工资,林维福发誓要挖掉穷根。
福建省永安市,在历史上就是全国有名的笋竹之乡,林维福的故乡贡川镇龙大村满山都是竹,乡亲们素来就有制作笋干的习惯,然而由于计划经济的制约,农民自产的笋干只能以每公斤3.5元的价格按任务指标卖给供销社,除了做成笋干卖给供销社外,几乎没有别的销路,春天里的笋多得可以用来做喂猪的饲料。林维福有他自己的算盘,在职辞前,因为出差,他曾到过江苏省的镇江市等城市,发现当地人有吃笋的习惯,他曾就当地笋干的价格和质量做过调查,发现永安当地生产的闽笋、贡笋质量好,价格却比江苏市场上的笋干低得多。看了那里的市场行情,决心靠笋吃笋博它一回。
这边赚那边亏,初涉商海就呛了苦水
辞职前的几天,林维福曾请事假前往江苏省无踢市考察,并在无锡市的盛岸农贸市场上以每月120元的租金租下了一个1.5米见方的摊位,又花120元在盛岸里42号租下了楼上楼下两个共70平方米的民房套间,靠着从乡亲好友那里借来的3万元资金,林维福兴冲冲找到贡川供销社,要求批发给他一批笋干,可是结果却令他失望。原来,那时永安市实行的是笋干统购统销政策,农民自产的笋干必须按指令性文件卖给供销社,而供销社的必须在完成省外贸下达的计划指标之后才能自主批发经营,当时贡川镇供销社还没有完成省外贸的计划指标,无法满足林维福的要求,因为有统购统销政策,林维福又不能直接向农民收购笋干,否则一但被乡里的干部发现了便会被以违反统购统销政策为由全部没收。
几天后,一筹莫展的林维福打听到与贡川镇毗邻的三明市三元区已取消了统购统销政策,他连忙赶到三明市三元区莘口镇一个历史上曾隶属永安的自然村,以每公斤10.02元的价格,买下了30件约1000公斤笋干和500公斤的黑木耳,通过零担托运发往江苏省无锡市。货物发走后,他立马带上妻儿和失学在家务农的妹妹林顺珠及另2名帮工赶到了无锡市。到达无锡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小妹妹和帮工将带去的笋干和黑木耳用水浸泡,再把笋干切成丝条。因为在辞职前几天的考察中,林维福有想过:笋干、木耳一类的干货在食用前必须用水浸泡,而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快,提前浸泡和切丝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泡多了又浪费,如果能先把笋干泡好,切成丝状,连同泡好的木耳搬到集市上去摆摊,销路一定会好。林顺珠和另2名帮工立即动手,第二天就把泡笋干和泡木耳摆到了集市上,果真俏销。一天下来,6个人温饱的费用已经不成问题。
原来笋干相当于压缩饼干,老家的竹农们在制作笋干时,都要把鲜笋先用大锅开水烫上10来分钟,冷却后再用支点压力25吨的木制千斤顶在2至3平方米的笋榨内榨上1至2个月,再用炭火烤上3天,这样一来,一棵硕大的鲜笋便变成了一块巴掌大的笋干片,其重量只有鲜笋的十八分之一;在制作泡笋丝的过程中,无异于把“压缩饼干”掺水还原,经过浸泡切丝后,其重量是原来的6倍,成本只需每公斤8至10元的笋干,经浸泡、切丝后,却可卖到每公斤4至6元,其价值是笋干的3至5倍。
当然,在卖泡笋丝的过程中,而林维福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开头几次,他泡切的笋丝料下多了卖不出去,到了第二天,毫无经验的林维福便把看上去成色很新的鲜切泡笋丝盖在昨天剩下的旧笋丝上,结果到了第3天,原先卖不完的旧笋丝便开始变霉变烂了,只好把霉变的旧笋丝倒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林维福采取了“限量浸泡,先卖旧后卖新”的经营策略,即平时每天只根据头一天的销量决定下料,一量有发现当天卖不完的旧货,第二天一定用开水烫过,然后把开水烫过的旧笋丝盖在刚切的新笋丝上,等卖完了旧笋丝,再卖新笋丝。这样良性循环,便不再有变霉变烂的笋丝了。
林维福绝不是那种只求温泡好农民,为了摆脱贫困他又背着自己从家乡带来的闽笋和黑木耳到农贸市场寻找别的摊点和食品公司、蔬菜公司去搞上门推销。永安的“闽笋”,在解放事前曾远销江苏、上海和香港东南亚地区,由于计划经济的束缚,直到90年初,在新一代的江苏人和上海人的印象中已很少有人知道永安闽笋了。在无锡市场上唱主角的是其它产区的笋干,林维福带去的永安闽笋很难打进当地市场。
一阵苦思瞑想之后,几天后林维福根据《永安市志》和《永安民间故事》上的记载,对自己的商品进行了一番文化包装,每到一处,林维福就说:“我手上的这种笋干曾经帮助中国制造过第一架飞机”,许多客商都感到奇怪,这时林维福便根据《永安市志》有榜有眼地说起了故事:清代未年的贡川镇有个叫李翔富的农民,拥有大片笋山,其笋干卖到上海并设有笋干商行,李翔富的儿子李宝俊靠着父亲卖笋的钱留学日本后,从事飞机制造研究,曾被清摄政王府电召回国制造飞机,于1911年6月21日试制成功并在北京南苑庑甸毅军操场上进行了试飞,辛亥革命后,李宝俊投奔南京临时政府,担任了陆军中校飞行营营长;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天折改为留守府,为了中国的航空事业,李宝俊又将其父李翔富交给他的信印办理了笋干抵押贷款,继续从事飞机制造。不幸因患痢疾于1912年8月26日在南京共和医院病逝。听这小子一说,不少客户都对林维福的笋干表示了兴趣。这样一来,林维福又把话题引到了永安闽笋制作的工艺上,说:“目前市场上的笋干大多是日晒的,色泽好,但是不够香,我们永安的闽笋是用炭火烤的,外朴内香,不信我可以留一点给你们试试,我这里有现成泡好的,你回去炒了吃后,如果不比市场上的笋干更香,我的这些干货样品你就把它扔了,如果好吃,你们帮我向顾客推荐,卖完了我再来拿钱。”这样一样,许多客户都愿意让林维福把样品留下试试。没有到过几天后回头客就来了,到了第2年3月回家永安时,林维福当初带去的笋干已销售一空,仅此一次就赢利1万元,但总的一算却净亏3万多元。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无锡的几个月里,林维福还从事过冬笋贩运,在推销笋干的过程中,他还时常向人讲起孟宗哭竹的民间故事,说的是历史上的永安贡川有个孟宗的孝子,有一天,孟宗的母亲病了很想吃笋,可是当时不是长笋的季节,孝子的孟宗便到竹林里去哭,一直哭到地上冒出了一棵竹笋。
这样一来,许多无锡人便对永安的冬笋感兴趣了。一看又有了赚钱的机会,林维福立马就向老家的哥哥发电报,让哥哥代他收购冬笋,并给他发货。头几趟,林维福还赚了一点,几天后各地冬笋大量涌进无锡,市场行情暴跌,有人传闻说上海已有做冬笋贩运的大户因行情不好跳了黄埔江,在江苏还有做冬笋贩运的人自己找到树上吊死了,林维福连忙向在老家的哥哥发电报,可他哥哥回电说定金已大量发放,林维福只好让哥哥继续去收购,结果在春节前几天,永安市的冬笋在市场上卖到了每公斤2.4元,运到无锡的冬笋只卖了每公斤3角钱。因为冬笋贩运中的失误,林维福就亏4万多元,两相对抵,净亏3万余元。
再博一回,还有机会爬起来
带着失望和惆帐的心理,林维福带着妻儿,回到了永安老家。听说他做生意亏了,债主们纷纷找上门来,一些债主就是还不缺钱也说自己正急着用钱。林维福的妻子急得直劝林维福:“我们不是做生意的料,你还是回原单位上班好了!”可林维福却说:“刚刚学游泳的人哪有不呛水的道理?如果我现在回原单位上班,领导还会接纳我,可是那3万元的债务怎么还?靠那总是人家的一半的工资,到老了都怕还不起啊!如果再博一回,咱们还有机会爬起来!”
面对纷纷上门的债主,林维福拿出了从别人那里借来的钱说:“我这次贩运冬笋亏了,这话不假,但没有亏掉十几万,这些钱先还给您,您如果还信得过我,便再借我一年!”就这样,林维福又一次向亲友们借来了3万元。2个月后林维福又从老家贩了一批笋干,带着妻儿赶到了无锡。
到了无锡,林维福还是摆摊卖泡笋,并到处推销笋干,与去年不同的是,这一次他再没有与他在老家的哥哥合伙搞贩运,而是与别人合作。他说:“兄弟之间做事,失误责任难分清,万一再次亏了也不致于把全家人都牵进去。”
重返无锡,他吸取了很教训,1990年9月从家乡带去的那批黑木耳经水泡后做成木耳也让他亏了一点。经水泡后,与东北木耳的口感不同,当地的无锡人喜欢松软的东北木耳,这次重返无锡,林维福也开始改卖水发东北木耳。原本价廉的笋干等干货,经水泡后,价值猛增。一年下来,他的那个摊位就让他赚了2万多元。考虑到品种的搭配,1993年,他还在自家租来的摊位上摆出了水发海带。这又是小本大利的一项奇招,每市斤1至2元的干海带,经水浸泡后,重量是原来的5倍,售价却可卖到每市斤5至8角钱。此后他陆续在自家的摊位上摆出了绿海带、水发黄花菜、扁尖笋、芹苔菜、海蜇丝等,至1999年已成为有15个品种的水发类蔬菜专营摊位。
在冬笋贩运方面,他采取了赶早不赶迟和赶小不赶大的做法。赶前不赶后是因为永安的纬度要比湘、浙、皖、赣等省区低,冬笋、春笋上市都要早几天,这时回永安抢购一批到无锡很少有对手,价格自然卖得高;赶小不赶大是因为竹笋都有大小年,遇到大年时,无锡的笋多、价低,林为福就趁早收手,遇到小年时,涌进无锡的笋少,林维福就多做几趟,有时家乡的冬笋不够销,他还跑到其它省份的毛竹产区去进货。有了这样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后再贩冬笋,果真让他赚了一笔不小的数目,此后即使有亏也亏得不多。恰巧那年在无锡市场上,桶罐装水煮笋的行情好,每桶的差价一般都在20元左右,了解到这一行情后,他立马就赶回福建,向人借了20万元,贩了一批水煮笋到无锡市场上,批零兼营,最远的还销到常州、张家港,结果赢利10余万元,他终于有了在商场起步的第一笔自有资金。
有钱大家赚,这叫“双赢”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翌年5月,当他回到故乡永安时,贡川人都在传闻林维福至少赚了三、五十万元,许多穷乡亲纷纷来找他取经,要林维福带他出去打工。当人们说起他至少赚了几十万时,他总是谦虚地说:“几十万是没有,总共赚十几万元是有,你们如果吃得了苦,跟我出去赚口饭吃还是有的。”结果,1993年5月,就有3个乡亲跟着林维福到了无锡,穷乡亲们刚到外地连吃住都成问题,林维福就在自己租来房间里打地铺让乡亲们住,还到农贸市场上帮乡亲们租好摊位,又教他们如何做水发菜,传授经营之道。结果那几位穷乡亲当年就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
几年的积累,已使林维福甩掉了穷帽。1995年春,小有积蓄的林维福回到永安老家,在贡川镇集市上为父母建起了一幢四层的别墅式小洋楼,同时给自己配了一个手机。
1996年,无锡市场上的桶罐装水煮笋行情看好,林维福看准时机,投资100多万元,从永安、湖南等孟宗竹产区贩去了一大批水煮笋,结果仅此一项就赚了30万元,加上每年贩运冬笋、水煮笋和雇请帮工经营的2个水发菜专营摊位的收入,自1999年这位昔日穷得连供妹妹上初中都无能为力的山里娃,连同在家乡贡川镇和无锡市的房产、存货等,其总资产已超过了一百万元。
如果说第一批随林维福到无锡市卖水发菜的穷乡亲,大多是沾亲带故的穷亲戚的话,那么,自从那幢会说话的四层小洋楼出现在贡川集镇后,陆续到无锡找林维福的人越来越多人,而且大多与他非新非故,其中还有三明市莘口镇的农民。随着到无锡市投奔林维福的穷乡亲越来越多,许多尚无着落的穷乡亲,大多依然只好挤在林维福的家里睡地铺,找不到摊位的穷乡亲指望着林维福给他帮助找摊位,一时手头紧的穷乡亲需要借钱应急,只好来找林维福;有的因为切成的笋丝几天卖不掉而变霉变烂,也愁眉苦脸地来找林维福,而林维福总是有求必应。刚开头的几年,最让他的妻子感到心烦的是,最多时竟有十几个尚无着落的穷乡亲吃住在家里,一餐饭下来,电饭煲要连烧几锅饭,前面一拨人吃饱了,后面一拨人轮着吃,直到那些穷乡亲都找到了摊位并让经营走上正轨,有了着落后,才会离去,有时前面一拨人走了,后面一拨人又来了,光煮饭就让人头疼。这样一来,林维福的妻子难免皱眉头,并且暗中有怨言。妻子的细微情绪,引起了林维福的注意,私下里,林维福心平气和地对妻子说:“一个好汉三个帮,这些穷乡亲都是国为看得起咱们才来投奔咱的,难道要象前些年那样,纷纷上门来向我们讨债心里才好受?再说他们也帮了咱们不少,自从他们来后,咱们有御货时,咱们这些穷乡亲都纷纷围上来帮忙了!”听林维福这么一说,本来就通情达理的妻子廖顺兰便想通了,说:“您说的也在理,自从这些穷乡亲来到这里后,你再也不用背着笋干挨家挨户去搞推销了”。林维福接着说:“有钱大家赚,你富我发大家发,用句时髦的话,这叫‘双赢’!”从那以后廖顺兰对前去求助的穷乡亲们的热心也不亚于林维福。
三明市莘口镇的农民林国喜,结婚几年了生活一直比较困难,千里迢迢找到林维福后,林维福便帮他找了摊位,又教他经营水发菜,林国喜没本钱,林维福便借给他成本或把自己的笋干、水发货赊欠给他。当地的一个地痞看林国喜的水发货摊位好赚钱,便找到了林国喜强行叫林国喜把摊位让给,说:“这个地方我要开,你到别处去开,别人敢欺负你,我会保护你。”林国喜不从,那个地痞便找岔子打他。知书达理的林维福便找到市场管理员,平息了纠纷。如今的林国喜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有十余万元存款。
在永安市郊区有个姓郑的农民,因为好赌,欠了一身债,冲着林维福到无锡去找到了林维福,林维福教他卖水发菜,可是水发菜生意是夫妻话,光靠他一个人很难完成,小郑只好去卖鲜蔬菜,没想到很快就把千余元的本钱给亏了,当他再一次找到林维福时,林维福先将自己的水发货赊给他卖,小郑偿到甜头后,又争取做妻子的工作,陆续把妻子和兄弟姐妹劝到了无锡,如今小郑还清了债,还有资产数十万元。
永安市贡川镇上有一位职工,平时好赌,他的农村妻子想让丈夫换个环境便让丈夫办了留职停薪手续,夫妻双双赶到无锡,要求林维福给他们找一条生路。林维福便把自己的摊位让给他们,那对夫妻跟着林维福和林国喜卖水发菜,几年后,丈夫改掉了赌博的恶习,回到单位上班,他的妻子继续在无锡卖水发菜,如今他们不仅还清了赌债,而且还有存款。
一位姓李的老乡,谈了个女朋友,可是因为男方的家里穷,女方的父母坚决反对,无奈之下,这时两情相悦的青年男女逃到了无锡,学着林维福他们卖水发菜,今年3月这对青年男女便带着自己挣来的数万元钱回到贡川老家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如今,跟着林维福到无锡做水发菜摊贩的永安人已达100多人,如果把这些人举家外出的水发菜摊贩在无锡的家庭人口都召集起来,已相当于永安山区的一个行政村。在无锡市的100多个市场上,90%有永安人和三明人开办的水发货摊点,而这些卖水发货的老乡几乎都找林维福取过经,或求他帮忙找过摊位,或赊他的笋干、水煮笋和现成的水发菜,或找林维福借钱应过急,有的还带着卖水发菜的发财技术闯到合肥、苏州和浙江省的长新市去开发市场。林维福没想到他自己从做泡笋,泡木耳开始的谋生手段居然在无锡、合肥等城市带出一个新兴的水发菜行业。许多在无锡、合肥等地做水发菜生意的乡亲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笋老大”。
“咱们的笋老大”,这句亲切的称呼来之不易。为了自己和乡亲们的致富,近年来,林维福付出了很多,到无锡10余年,林维福只回永安过了一个春节,每年除夕和正月初一他照样营业,最忙的季节,他每天只睡3个小时,26个小时才吃一餐饭。
有句古话叫着“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可林维福带领穷乡亲外出打工致富的经历却恰恰相反,非但没有“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反而带出了城市人的新的消费习惯,随着水发菜产业规模效益的形成,笋干销售量增加了,林维福这个从事跨省营销的“笋老大”再也不用背着笋干挨家挨户去推销了,他因此可以腾出更多的精力来做大批量的长途贩运,这实在是一种的“双赢”的选择。当林维福成为身家百万的小富翁时,他的故乡永安市和贡川镇的领导也从他的身上看到了笋竹之乡的希望之光,至1998年,永安市不仅早已取消了笋干统购统销政策,贡川镇党委、政府还成立了农副产品营销协会无锡分会,推选林维福为会长;1999年,当时的永安市市长陈美绵曾赶到无锡市八达食品商城14号,把一块精美的“永安笋业同业公会无锡分会”的牌匾交给了永安市笋业协会副会长、无锡分会会长林维福,永安市的领导还勉励他:“壮大营销队伍,让永安竹业产品走向世界”。2000年,永安市被农业部授予“中国笋竹之乡”称号,目前,这个市正在兴起一股科学育竹热和竹乡森林旅游热。2002年5月,林维福被授予福建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永安市竹业协会还为林维福精心设计了带有永安竹神肖像和永安竹业微标的精美名片。
(后记:通过采访林维福,笔者看到水发菜产业是个大有“钱”途的新兴行业,尤其适合那些肯吃苦而又希望只有三、五千元小本就能够谋生起家的打工者,除了有个栖身的住处和一个2至3平方米的小摊位,再加几个水缸、售货盆之类的小物件,便可让自己当老板了)
页面执行:3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