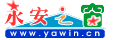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一(1)
郑伯克段于鄢(左传)
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
本文和以下三十三篇都选自《左传》。《左传》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尤长于写战争,写外交,寥寥数语,就把复杂的事情讲得明白生动。因此,有人赞它“艳而富”,对后世影响极大。本书选录《左传》也最多。
郑庄公一家因争夺君位而闹得兵戎相见,兄弟相残,母子翻脸。亏得颍考叔这有心人,才使他母子和好。历来认为这是个道德问题,其实更是个制度问题。祸根就在君主专制,引起野心家们不断投入这场赌博。“赌博场中无父子”,唐太宗尚且杀了亲兄弟建成元吉,何况郑庄公?所以有人说:一部《二十四史》,就是一部“相斫书”。直到上个世纪,还有人扮演共叔段的角色,再次印证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古话。本文写郑庄公的阴险,颍考叔的机智,都是传神之笔。
初①,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②。生庄公及共(gōng)叔段。庄公寤(wù)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wù)之③。爱共叔段,欲立之。亟(qì)请于武公,公弗许。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④。公曰:“制,岩邑也,虢(guó)叔死焉⑤,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taì)叔⑥。
【注释】
①初:当初。古文追述往事时常用此词。②郑武公:姓姬,名掘突,郑国第二代国君主。申:国名,姜姓,今河南南阳县。武姜:“武”表示丈夫为武公,“姜”是她娘家的姓。③寤生:逆生,即胎儿出生时先下脚。寤,通“牾”。恶:憎恨,讨厌。④之:代词,指郑庄公。制:地名,又名虎牢,今河南巩县东。⑤虢叔:东虢国的国君。“制”原是东虢国领地。东虢国在前767年已经被郑国吞并。⑥京:郑邑名,今河南荥阳县东南。大:同“太”。下同。
祭(zhaì)仲曰①:“都城过百雉(zhì)②,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③;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④?”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⑤。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⑥。子姑待之。”
【注释】
①祭仲:郑大夫。春秋时,大夫位于卿之下,士之上。人数较多,且分等级。后世为中级以上文官,如御史大夫、谏议大夫,因此大夫也作文官的通称。②雉:量词。古代计算城墙,长三丈、高一丈为雉。③参:同“三”。④辟:古“避”字。⑤滋蔓:滋长蔓延。⑥毙:倒下去。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①。公子吕曰②:“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③。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④。”公曰:“不义不昵(nì)⑤,厚将崩。”
【注释】
①鄙:边邑。贰:两属,归两方管理。②公子吕:字子封,郑大夫。③廪延:郑邑名。今河南延津县北。④厚:指土地扩大,势力雄厚。⑤昵:亲近。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shèng)①,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yān)②,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③。
【注释】
①缮:修理,制造。甲:铠甲。兵:武器。卒:步兵。乘:兵车。②鄢:郑地名,今河南鄢陵县境。③五月辛丑:即鲁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共:古国名,今河南辉县。后被卫国吞并。段出奔共,故称共叔段。
书曰①:“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②。不言出奔,难之也。
【注释】
①书:指《春秋》原文。②郑志:郑伯的意图。《春秋》暗指郑伯存心不良。
遂置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①:“不及黄泉②,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③,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④,请以遗(weì)之⑤。”公曰:“尔有母遗,繄(yī)我独无⑥!”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⑦,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yì)⑧。”遂为母子如初。
【注释】
①城颍:郑邑名,今河南临颍县西北。②黄泉:地下的泉水,也指阴间。③颍考叔:郑大夫。颍谷:郑国边境的都邑,今河南登封县西南。封人:管理疆界的官。④羹:有汁的肉食。⑤遗:给,留给。⑥繄:句首语气词。⑦阙:挖掘。⑧泄泄:快乐舒畅的样子。
君子曰①: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kuì),永锡尔类②。”其是之谓乎?
【注释】
①君子曰:《左传》作者以发表评论的方式。君子是有道德和见解的人物。②《诗》:《诗经》。引文见《诗经•大雅•既醉》。匮:穷尽。锡:同“赐”,给予。类:同类的人;朱熹解释为“善”
【译文】
当初,郑武公从申国娶来夫人,名叫武姜,生下庄公和共叔段兄弟俩。庄公生时难产,惊动了姜氏,起名寤生,不喜欢他,偏爱共叔段,总想立为太子,多次求武公,武公一直不肯答应。庄公一登位,姜氏便要求把制邑封给共叔段。庄公说:“制可是个险地,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封给弟弟不大好。其他地方,随你挑选,我惟命是从。”姜氏便要求京城,庄公同意共叔段住到那里。从此,人们称他京城太叔。
祭仲说:“一般的城池,如果城墙超过一百雉,就会成为国家的祸害。先王规定:大城不得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得超过五分之一,小城不得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城超过规定,不合制度。只怕将来你会受不了。”庄公说:“姜氏要这么做,我怎能避免祸害呢?”祭仲说:“姜氏的欲望哪能满足!不如早作安排,以免祸根蔓延。蔓草都难除掉,何况是你宠爱的亲弟弟!”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吧!”
不久,太叔指使西部和北部边区暗中归附他。公子吕对庄公说:“一国不能有二主,你究竟怎么打算?如果想让给太叔,就让我去侍奉吧!如果不,那就该除掉他,莫使百姓多心。”庄公说:“何必呢?他会自作自受的。”
后来,太叔率性把那两处收归已有,直扩展到廪延一带。公子吕又说:“该动手了!他地盘扩大了,势力会膨胀起来。”庄公说:“他对国君不尽义,对兄长不亲近,土地越多,垮得也越快。”
太叔修治城郭,赶造武器,征调士卒和战车,就要偷袭郑都了。姜氏也准备开城门接应。庄公打听到他动手的日期,说:“现在可以了!”马上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攻打京城。京城人背叛了太叔段,太叔只好逃入鄢邑。郑伯又亲自率兵攻鄢,五月辛丑这天,太叔逃出郑国,投奔共国去了。
《春秋》写道:“郑伯克段于鄢。”意思是说:太叔不守孝弟之道,所以不称他“弟”。这事如同两国交战,所以用了“克”字。称庄公为“郑伯”,是讥刺他对弟弟不加管教,早有杀弟的阴谋。又不明说太叔出奔,实在是难得说清楚啊。①
于是把姜氏安置在边远的城颍,并对天发誓:“不到黄泉,决不再见!”不久又后悔了。
颍考叔正在颍谷担任封人,掌管疆界事务,听说这事,便借进贡为由,来见庄公。庄公赐宴,颍考叔故意把肉挑出来放一边。庄公问他什么意思,他说:“小人有母,小人带回去的东西她都吃过了。可是还未尝过国君的菜肴,请求让我带给她吧!”庄公叹道:“你有母亲可以孝敬,我偏没有啊!”颍考叔很奇怪:“这话怎么说呢?”庄公便一五一十告诉他,说自己很后悔。颍考叔说:“您何必为此发愁呢?如果挖开地面,掘到泉水,母子在隧道会见,岂不就应了誓言,谁能说你不是呢?”庄公就照他的话去办。庄公进入地道,赋诗说:“进入地道中,其乐也融融!”姜氏走出地道,也赋诗说:“走出地道外,心情多畅快!”于是母子和好,跟当初一样。
君子说:“颍考叔真是纯孝呀!他不但爱自己的母亲,而且影响到庄公。《诗经》说:‘孝子行孝无穷尽,永远感化同类人。’大概讲的就是这类情况吧!”
①此句亦译:“实在是责备他们”。
周郑交质(左传)
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
郑伯是周王的近亲,父子两代都任周王的卿士。周朝自平王东迁以后,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实际上已经衰落。对外不得各国诸侯的尊重,对内又不能掌握实权,于是发生了“周郑交质”这件事。称周郑为“二国”,就含有讥讽周朝衰落的意思。后来各诸侯国常有交换人质的事,由于互不信任的缘故,结果也多不妙。但也并非完全不起作用,本书卷四《触龙说赵太后》即是一例。
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①。王贰于虢②,郑伯怨王③。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④。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⑤。王崩,周人将畀(bì)虢公政⑥。四月,郑祭(zhài)足帅师取温之麦⑦;秋,又取成周之禾⑧。周郑交恶。
【注释】
①卿士:执政大臣。郑武公及郑庄公父子先后以诸侯的身份在周王朝做卿士,兼掌王室实权。②贰:贰心,此指周平王不信任郑庄公。虢:指西虢公。③郑伯:指郑庄公。④质:人质,双方互相用亲子或贵臣作抵押取信,称为交质。⑤王子狐:周平王的儿子。郑公子忽:郑庄公的儿子。⑥畀:授与,托付。⑦祭足:即祭仲。温:周地,今河南温县西南。⑧成周:周地,即洛邑,今河南洛阳市东郊。
君子曰:“信不由中①,质无益也。明恕而行,要(yāo)之以礼②,虽无有质,谁能间(jiàn)③之?苟有明信,涧溪沼沚之毛⑤,蘋蘩薀藻之菜⑤,筐筥(jǔ)锜(jǐ)釡(fǔ)之器⑥,潢(huáng)污行潦(lǎo)之水⑦,可荐于鬼神,可羞于王公⑧。而况君子结二国之信⑨,行之以礼,又焉用质!《风》有《采蘩》《采蘋》⑩,《雅》有《行苇》《泂(jiǒng)酌》,昭忠信也。”
【注释】
①中:同“衷”,内心。②要:约束。③间:挑拨离间。④涧溪:山中小河,沼:池塘。沚:小洲。毛:野草。⑤蘋:四叶菜,又叫田字草。蘩:即白蒿。薀藻:一种喜欢聚生的水草。即金鱼藻。⑥筐筥:盛物的竹器,方形为筐,圆形为筥。锜:有三只脚的釡。釡:锅。锜、釡都是容器、炊具。⑦潢污:停积的死水。行潦:路旁的积水。⑧荐:向鬼神进献物品,特指不用猪、牛、羊的祭祀。羞:美味的食品。这里作动词用。⑨君子:春秋时代通指统治者和贵族男子。⑩《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采蘩》、《采蘋》都是《国风•召南》中的诗篇。《雅》:指《诗经》中的《大雅》、《小雅》。《行苇》、《泂酌》都是《大雅•生民之什》中的诗篇。
【译文】
郑武公、郑庄公相继做周平王的卿士。周平王打算兼用西虢公,郑庄公埋怨平王。周平王说:“没有这回事呀!”为了消除疑忌,双方交换人质。周平王的儿子姬狐去郑国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姬忽去成周做人质。周平王死了,周人准备让虢公执政。四月,郑国大夫祭足率兵抢割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割了成周的谷子。从此周朝和郑国就互相仇视。
君子说:“不是出自内心的信任,就是交换人质也没有用啊!如果双方都能实行恕道,按礼办事,即使没有人质,谁又能从中挑拨离间呢?如果真是光明磊落,开诚相见,那么,山涧小池的水草,浮萍白蒿一类的野菜,竹篮瓦钵一类的器具,低地积水或路上的流水,也可以拿来祭祀鬼神,进献王公。何况君子结成两国之间的信任,按礼行事就成了,何必交换人质呢?《国风》中有《采蘩》、《采蘋》,《大雅》中有《行苇》、《泂酌》,这些诗篇都是昭明忠信的啊!”
石碏谏宠州吁(左传)
隐公三年(公元前720年)
“宠”就是溺爱。宠子必骄,骄子必败。何况州吁是国君的宠妾所生,在国君死后,必定会与国君的嫡子争权夺位,酿成祸乱。石碏主张教子以“义方”,不让儿子走上邪路。这本是做父母应有的基本常识,不幸的是有些父母偏偏不懂。所谓“六顺”、“六逆”,只是古代贵族的伦理;但“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在现代社会也是应当做到的。唐代柳宗元写过一篇《六逆论》,认为“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这三项,“虽为理国之本可也,何必曰乱?”
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①,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②。又娶于陈,曰厉妫(guī)③。生孝伯,蚤死④。其娣(dì)戴妫⑤,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
【注释】
东宫:太子所住的宫室,故太子也称东宫。②《硕人》:《诗经•卫风》篇名。③妫:陈国为妫姓。厉和下文的戴,都是谥号(古时有地位的人死后所得称号。)④蚤:通“早”。⑤娣:春秋时代,诸侯娶他国之女为妻,有妹妹或侄女随嫁,叫娣。
公子州吁,嬖(bì)人之子也①。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碏(què)谏曰②:“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③;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zhěn)者,鲜(xiǎn)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④。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⑤。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弗听。
其子厚与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⑥。
【注释】
①嬖:宠爱。②石碏:卫国的大夫。③眕:安定的样子。鲜:少。④六逆:庄姜为正妻,桓公为子,是贵、是长、是亲、是旧、是大; 嬖为妾,州吁为庶子,是贱、是少、是远、是新、是小。⑤速:招致。⑥老:告老退休。
【译文】
卫庄公娶了齐国太子得臣的妹妹,名叫庄姜。庄姜美而无子,卫国人为他做了一首题为《硕人》的诗。庄公又从陈国娶妻,名叫厉妫。厉妫生孝伯,早死。厉妫的妹妹戴妫生了桓公,庄姜便把桓公当作自己的儿子。
公子州吁是卫庄公宠姬所生,受到庄公宠爱。他爱玩刀弄矛,庄公也不禁止。庄姜很讨厌他。
石碏劝庄公说:“臣听说,疼爱儿子,应当用正道教育他,防他走上邪路。骄横、奢侈、纵欲、放荡,是走上邪路的开端;这四种恶习的养成,又是因为宠爱过份、赏赐太多的缘故。如果要立州吁为太子,就早点定下来;如果不,就怕养成祸乱。受到宠爱而不骄傲;骄傲还能接受约束;接受约束而不埋怨;埋怨还能克制自己;这样的人很少很少。再说,卑贱的妨害尊贵的,年轻的凌辱年长的,关系疏远的离间关系亲近的,新进的离间先来的,名位低的压制名位高的,淫乱的侵犯正直的,这叫做六逆。君能合乎礼义、臣能执行君命、父慈、子孝、兄爱、弟敬,这叫做六顺。抛弃六顺,鼓励六逆,必定招来祸患。做君主的,应当尽力除去祸患,现在却反而去招来祸患;这样恐怕很不妥当吧?”庄公不听规劝。
石碏的儿子石厚常跟着州吁混,禁也禁不住。卫桓公继位了,石碏便告老还家。
相关内容:
页面执行:3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