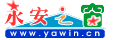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一(4)
僖公五年(公元前655年)
“假道伐虢”,是大国侵略小国的阴谋。只有像虞公这样贪小利的愚人,才会上当。宫之奇劝他的时候,提出两个论点。一是“鬼神惟德是依”,“民不和,神不享”,这与《季梁谏追楚师》中的观点相同。二是邻国之间有“唇齿相依”的关系,允许晋国假道灭虢是极端错误的,等于“开门揖盗”,自取灭亡。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①。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②。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③。一之为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④,其虞虢之谓也。”
【注释】
①晋侯:姬姓。此时的晋侯是晋献公。复:又。三年前晋军已借道一次。假:借。虞:国名。虢:国名。都在今山西平陆县。②宫之奇:虞大夫。表:屏障。③寇:外来的敌军。玩:忽视。④辅:车旁夹板。或说,辅以喻颊骨,车比喻牙床。
公曰:“晋,吾宗也①,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②。大伯不从,是以不嗣③。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④;为文王卿士⑤,勋在王室,藏于盟府⑥。将虢是灭,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⑦,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而以为戮,不唯逼乎⑧?亲以宠逼⑨,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注释】
①宗:同祖为宗。晋、虞、虢均为姬姓国。②大王:太王,周文王的祖父。大伯:太伯,太王的长子。虞仲:太王的次子。昭、穆:古时帝王的宗庙里设有神位,始祖居中,后世祖依次左右排列。排在左边的称“昭”,排在右边的称“穆”,昭位之子在穆位,穆位之子在昭位,这样左右更叠,分别辈次。③不从:太伯是长子,本应继承王位,但他认为小弟季历的儿子姬昌(即后来的周文王)有“圣德”,就和二弟仲雍一道出走。④虢仲、虢叔:虢的开国祖先,周文王的弟弟。虢仲封东虢,已于前767年为郑所灭。虢叔封西虢,即本文中所指之虢。⑤卿士:执掌国政的大臣。⑥盟府:主管盟誓典策的官府。⑦桓、庄:晋献公的同祖兄弟。⑧逼:迫近,威胁。⑨宠:尊贵。
公曰:“吾享祀丰洁①,神必据我②。”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③,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④。’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⑤。’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⑥,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⑦,神其吐之乎?”
【注释】
①享祀:祭祀。②据:依附。既依附,则必保佑。③实:是,提前宾语。④《周书》:古书名。所引句子已佚。辅:助。指保佑。⑤馨:散布很远的香气。古人以为,鬼神闻到香气就是享用了祭品。⑥冯:通“凭”。⑦荐:进献。
弗听,许晋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腊矣①。在此行也,晋不更(gēng)举矣②。”冬,晋灭虢。师还,馆于虞③。遂袭虞,灭之。执虞公④。
【注释】
①腊:年终的祭祀典礼。②更:再。举:起兵。③馆于虞:晋兵驻在虞国客馆。④执:捉住。
【译文】
晋侯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虞公说:“虢是咱们虞国的屏障,虢国一亡,虞也会跟着灭亡。晋国的贪心,万不可助长;敌人的阴谋,万不可小看。上次借路已经错了,怎么可能再借呢?俗话说:‘颊骨靠牙床,唇亡而齿寒’,虞虢两国正是这样啊!”
虞公说:“晋国和我同宗,难道会害我吗?”宫之奇说:“当年泰伯和虞仲,是太王的长子和次子,泰伯不从父命,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都是王季的儿子,又都做过文王的卿士,为王室建立了功勋,他们受封的典策还藏在盟府。晋侯既要灭虢,怎么还爱惜虞国呢?再说,虞虽是晋的同宗,能比桓叔、庄伯的子孙更亲吗?桓叔、庄伯的子孙有什么罪?为什么都被杀掉?还不是因为他们是亲贵,威胁到晋侯的权位吗?近亲威胁到他,还要杀掉,何况是个国家呢?”
虞公说:“我祭神的时候,供品又丰盛又干净,鬼神必定保佑我。”宫之奇说:“我听说,鬼神并不偏爱谁,只保佑那有德的人。所以《周书》说:‘上天不分亲疏,只保佑有德之人。’又说:“并非黍稷香味馨,德行之香通鬼神。”又说:‘献上祭品彼此相同,唯有那些有德之人献上的,鬼神才肯享用。’由此可见,如果缺了德行,百姓不会听从他,鬼神也不会保佑他。假若晋侯灭了咱们虞国,但他崇尚德行,献上祭品,难道神灵会吐掉不吃吗?”
虞公不听劝告,还是答应了晋国的请求。宫之奇便带着全族逃走了。他说;虞只怕来不及举行年终的腊祭了。晋国这一回就会灭掉虞国,不必下次动兵。”
这年冬天,晋灭掉虢国。晋军回来,在虞国借住,突然袭击,把虞国灭掉,把虞公也捉去了。
齐桓下拜受胙(左传)
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
周朝自平王东迁以后,王室渐衰;但是诸侯国都还不够强大,齐桓、晋文都要利用天子的名义,才好挟制一些小国,充当霸主。于是齐桓公在葵丘来了一场出色的表演。本文结尾四字,一字一顿,把齐桓公那毕恭毕敬的作秀,写得活灵话现。
夏,会于葵丘①。寻盟②,且修好,礼也。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zuò)③,曰:“天子有事于文武④,使孔赐伯舅胙⑤。”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以伯舅耋(dié)老⑥,加劳⑦,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顏咫(zhǐ)尺⑧。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⑨,无下拜?恐陨越于下⑩,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注释】
①葵丘:今河南兰考县境内。②寻:重申旧事。前一年,齐桓公曾在曹国会集诸侯,所以这次集会称“寻盟”。③宰孔:宰是官,孔是名,周王室的卿士。齐侯:指齐桓公。胙:祭祀用的肉。周王赐给异姓诸侯祭肉,是一种优礼。④文武:周文王和周武王。事:指祭祀。⑤伯舅:天子称异姓诸侯叫伯舅。因周王室与异姓诸侯通婚。⑥耋:年七十为耋。⑦加劳:加上有功劳于王室。周襄王因得齐桓公的支持,才能继承王位。⑧咫:八寸。咫尺:形容很近。⑨小白:齐桓公名。⑩陨越:坠落。
【译文】
夏天,齐桓公在葵丘与各国诸侯聚会,为的是重申原来的盟誓,使大家更加和好。这是合乎礼的。
周襄王派宰孔赏赐齐侯一块祭肉。宰孔说:“天子正忙于祭祀文王、武王,特派我来,赏赐伯舅一块祭肉。”
齐侯刚要下阶拜谢。宰孔说:“且慢,后面还有命令哩。天子命我告诉您:‘伯舅年纪大了,加之对王室有功,特赐爵一级,不必下阶拜谢。’”齐桓公答谢:“天子的威严,离我不过咫尺,小白我岂敢贪受天子之命‘不下拜’?果真那样,只怕就会垮台,使天子也蒙受羞耻。怎敢不下阶拜谢!”
下阶,拜谢;登堂,领赏。
阴饴甥对秦伯(左传)
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5年)
晋惠公本是秦穆公的舅老爷,他靠姐夫的帮助,回国登了君位;却以怨报德,和秦国打了一仗,结果兵败被俘。阴饴甥在这时奉命到秦国求和,实在尴尬得很。但是,他在回答秦穆公的时候,巧妙地将国人分为“君子”、“小人”两部分,一正一反,既承认晋侯不是,向秦服罪;又表明晋国的士气不可轻侮。软硬兼施,说得不亢不卑,恰到好处。因此赢得秦穆公的尊敬,决心做个顺水人情,放回晋惠公,以提高自己的威信。
《古文观止》编者吴楚材的评语,说本文用的是“整对格”。现代学者钱伯城解释:整对格就是名与名对,段与段对。以本文来说,“君子”与“小人”对,“报仇”与“报德”对,“威”与“恕”对,“怀德”与“畏刑”对。内容含意上的正反开合,则是意与意对。这种整对格,骈散结合,在唐以后的散文中,以韩愈为代表,曾被大量运用。
十月,晋阴饴甥会秦伯①,盟于王城②。
秦伯曰:“晋国和乎?”对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丧其亲③,不惮(dàn)征缮以立圉(yǔ)也④,曰:‘必报仇,宁事戎狄。’君子爱其君而知其罪,不惮征缮以待秦命⑤,曰:‘必报德,有死无二⑥。’以此不和。”秦伯曰:“国谓君何?”对曰:“小人戚⑦,谓之不免;君子恕,以为必归。小人曰:‘我毒秦⑧,秦岂归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归君。’贰而执之,服而舍之⑨,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怀德,贰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纳而不定,废而不立,以德为怨,秦不其然。”
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馆晋侯⑩,馈(kuì)七牢焉○11。
【注释】
①阴饴甥:晋大夫。秦伯:指秦穆公。②王城:今陕西朝邑县西南。③小人:指缺乏远见的人。君:指晋惠公。他借秦穆公的力量才做了国君,后来和秦发生矛盾,在战争中被俘。④惮:怕。征缮:征集财赋,修缮兵器,准备打仗。圉:晋惠公的太子名。⑤君子:指晋国的有远见的贵族。待秦命:这是委婉的说法。真正意思是:如果秦不送回我们的国君,就不惜一切,再打一仗。⑥必报德,有死无二:报答秦国对晋的恩德,至死没有二心。⑦戚:忧愁、悲哀。⑧毒:毒害,得罪。指晋惠公与秦为敌。以前晋国发生灾荒,秦国输送了粮食;后来秦国发生灾荒,晋国一点也不给。⑨贰:背叛。舍:释放。⑩改馆:换个住所,改用国君之礼相待。○11馈:赠送。七牢:牛、羊、猪各一头,叫做一牢。七牢是当时款待诸侯的礼节。
【译文】
鲁僖公十五年十月,晋国的阴饴甥会见秦伯,两国在王城结盟。秦穆公问他:“你们晋国内部意见和协吗?”阴饴甥说“不和。小人以失去国君为耻,又因丧失亲人而悲伤,不怕多征赋税,舍得花钱添置武器盔甲,并且拥立太子圉继任国君。他们说:‘宁肯奉事戎狄,也得报这个仇。’君子则爱护自己的国君,但也知道他的罪过。他们也不怕多征赋税,舍得花钱添置武器盔甲,却是为了等待秦国的命令。他们说:‘一定得报答秦国的恩德,有死无二,’这样,意见就不一致。”
秦穆公又问:“你们对国君的命运有什么看法?”阴饴甥说:“小人发愁,认为国君不免灾祸;君子宽心,以为国君必定回来。小人说:‘我对秦国太毒了,秦国岂肯还我国君?’君子说:‘我已认罪了,秦国必定还我国君。’他背叛了,就抓起来;他认罪了,就放回来。恩德再没有比这更厚的了,刑罚也没有比这更威严的了。内心臣服的自然感恩怀德,那怀有二心的也会畏惧刑罚。这一仗如此了结,秦国真可成就霸业了。不然的话,当初帮他回国登位,又不让他安于其位;后来废了他的君位,又不让他复位,以致原来施的恩德,反变成仇恨,秦国总不会出此下策吧!”
秦穆公说:“你讲的正合我心啊!”马上就让晋侯改住宾馆,赠送七牢,以诸侯之礼相待。
子鱼论战(左传)
僖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38年)
宋襄公受了楚成王的愚弄,妄想充当霸主,既要挑起战争,又要假仁假义,结果一再错过战机,打了败仗,成为千古笑柄。近代史学家吕思勉认为,此事反映了新旧两派治兵的分歧。美国华人学者黄仁宇说,春秋时的车战,是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离不开“礼”的束缚。
楚人伐宋以救郑①。宋公将战②。大司马固谏曰③:“天之弃商久矣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⑤。”弗听。及楚人战于泓⑥。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⑦,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⑧。
【注释】
①伐宋以救郑:宋襄公率领许、卫等国讨伐郑国,楚人伐宋以救郑。②宋公:宋襄公。③大司马固:即公孙固,即下文中的“子鱼”。司马是统率军队的高级长官。④天之弃商:宋是商朝的后代,这时周灭商已四百多年。⑤弗可赦也已:不可原谅,不可能。⑥泓:宋国河流,今河南省柘城县西北。⑦陈:古“阵”字,作动词用。
⑧门官:国王的卫队。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chóng)伤①,不禽二毛②。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ài)也③。寡人虽亡国之余④,不鼓不成列⑤。”
【注释】
①重伤:伤害已经受伤者。②禽:同“擒”。二毛:头发黑白相间的人,将近年老的人。③阻隘:险阻之地。④寡人:国君自称。亡国之余:宋是商朝后代,所以宋襄公这样说。⑤鼓:击鼓进攻。
子鱼曰:“君未知战。勍(qíng)敌之人①,隘而不列,天赞我也②。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gǒu)③,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④?若爱重伤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⑥,金鼓以声气也⑦,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⑧,鼓儳(chán)可也⑨。”
【注释】
①勍,强。②赞:助。③胡耇:老人。④勿:不。重:再。⑤爱:怜惜。⑥三军:春秋时代,大的诸侯国有上、中、下三军,泛指军队。⑦金:金属制成的响器(相当后代的锣)。古代作战,击鼓进军,鸣金收兵。气:士气。⑧致志:鼓起士兵的战斗意思。⑨儳:不整齐。没有摆成阵势。
【译文】
楚国攻打宋国,为的是援救郑国。宋襄公打算迎战。大司马子鱼劝阻,说:“上天抛弃商朝已经很久了,你却想复兴它,这样违反天命,上天不会饶恕的啊!”宋襄公不听。
宋楚两军在泓水交战。宋军已摆好阵势,楚军还没全部渡河。大司马说:“彼众我寡,趁他还没渡完,请下令攻击。”襄公说:“不行!”楚军都渡过了,还没摆好阵势,大司马又请下令攻击,襄公还是说:“不行!”等楚军摆好阵势,宋军才进攻,结果大败。襄公伤了腿,他的卫队也被歼灭。
国人都责备襄公。襄公说:“有德的人打仗,敌人已经受伤,就不再伤他;敌兵头发半白,就不俘虏他,古时候指挥作战,是不利用地形之险的。寡人虽是已经亡了的商朝的后代,却不能钻敌人尚未布阵的空子,发动进攻。”
子鱼说:“君主简直不懂战争啊!敌人强大,因地形不利而未摆好阵势,真是上天帮忙。趁机发动攻势,有何不可?只怕还没有把握取胜哩。何况那拼死战斗的,都是我们的敌人,即使是老头,能抓就抓过来,至于那头发花白的,更不必怜惜了。古人说:‘明耻教战’,就是要鼓舞士气,消灭敌人。敌人虽受了伤,但他还在作战,怎么能不再杀伤他?如果可怜他再次受伤,当初就不该伤他;如果怜惜头发半白的敌人,当初就该向敌人屈服。军队作战,就是要利用天时地利,并且鸣金击鼓以激励士气。敌人为险隘所阻,我们趁机攻击,正是理所当然。敌人阵势尚未布好,我们击鼓鸣金,发动攻势,也是理所当然。”
相关内容:
页面执行:3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