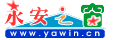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二(5)
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
楚灵王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子革却顺着他,三问三答,都是随声附和,旁观者都嫌他肉麻。其实他是欲擒先纵,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利用周穆王的故事,一下击中楚灵王的要害,使他内心震动,坐卧不安。这种进谏方式,非常奇特。文章描写灵王的服饰和动作,更烘托出他那骄横的气概。
楚子狩于州来①,次于颍尾②,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③,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④,以为之援。
【注释】
①楚子:楚灵王,即公子围,他是楚共王庶出的儿子。前540年至前529年在位。狩:冬季打猎。此处指楚王出游。州来:古小国名,春秋时属楚,后为吴所灭。②颍尾:颖水下游入淮河处。③荡侯:他与以下四人,都是楚大夫。徐:小国名,在吴、楚之间。④乾溪:今安徽亳(bó)县。
雨(yù)雪①,王皮冠、秦复陶、翠被(pì)、豹舄(xì)②,执鞭以出。仆析父从③。右尹子革夕④,王见之,去冠、被,舍(shě)鞭⑤,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⑥,与吕伋、王孙牟、燮(xiè)父、禽父并事康王⑦。四国皆有分⑧,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⑨,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⑩,筚(bì)路蓝缕○11,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12,以共御王事○13。齐,王舅也○14;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15。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16,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17,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注释】
①雨雪:下雪。②皮冠:皮帽。秦复陶:秦国赠的羽衣。翠被:用翠羽装饰的披肩。舄:鞋。③仆析父:楚大夫。④右尹:官名。夕:晚上谒见。⑤舍:放下。⑥熊绎:楚国始祖。⑦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齐、卫、晋、鲁四国的始祖。康王:即周康王,周王第三代。⑧四国:指齐、卫、晋、鲁。⑨鼎:夏、商、周三代视为传国之宝。⑩辟:同“僻”。荆山:楚人的发祥地,今湖北南漳县西。○11筚路:柴车。蓝缕:破烂的衣服。○12桃弧棘矢:桃木做的弓,棘木(酸枣木)做的箭。○13共:同“供”。 ○14齐,王舅也:周成王的母亲是姜太公的女儿。○15昆吾:楚的远祖,曾住在许地。许:周初分封的诸侯国。○16陈、蔡:本为周武王所封的诸侯国,后来为楚所灭。不羹:地名,有东西二邑。赋:指兵车。○17四国:指陈、蔡、和东西不羹。
工尹路请曰①:“君王命剥圭以为戚柲(bì)②,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③,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④,王出,吾刃将斩矣⑤!”
【注释】
①路:人名。“工尹”:工官之长。②剥:破开。圭:玉制礼器。戚:斧头。柲:柄。③响:回声。责备子革随声附和。④厉,磨刀石。须:等待。○5刃:刀口。
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①。王曰:“是良史也②!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③。”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④,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zhài)公谋父作《祈招(sháo)》之诗以止王心⑤,王是以获没于祗(zhī)宫⑥。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yīn)⑦,式昭德音⑧。思我王度⑨,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⑩,而无醉饱之心。’”
【注释】
①左史:官名。周代史官有左史、右史之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倚相:人名。②是:代指倚相。③《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皆上古书名,早已佚失。④穆王:周穆王,西周第六代,相传曾周游天下。古小说《穆天子传》记其西游故事。肆:放纵。⑤祭公谋父:周朝的卿士。《祈招》之诗:《诗经》无此篇。⑥祗宫:穆王的别墅。⑦愔:镇静和乐的样子。⑧式:语首助词。昭:明。⑨度:仪表、行为。⑩形:同“型”,有衡量的意思。
王揖而入。馈(kuì)不食①,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②。
仲尼曰:“古也有志③:‘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④!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注释】
①馈:向尊长进食物。②及于难:前529年,即子革对灵王后的第二年,楚国内乱,灵王兵溃逃走,途中自缢而死。③仲尼:孔子。志:记载。④信:真正,的确。
【译文】
楚灵王到州来阅兵狩猎,驻扎在颍尾,派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领兵包围徐国,以威胁吴国。他自己进驻乾溪,作为后援。
天正下雪,灵王头戴皮帽,身穿秦国赠送的羽衣,外加翠羽披肩,脚踏豹皮鞋,手执鞭子走出来,仆析父随从他。右尹子革晚上来朝见,灵王接见他,摘下帽子,脱下披肩,放下鞭子,同他谈话,说:“从前我们先王熊绎,和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一起侍奉周康王,四国都赏赐了宝器,唯独我楚国没有。现在我如果派人去成周,要求把宝鼎赐我,周天子肯吗?”子革说:“当然肯给君王呀!从前我先王熊绎,僻处荆山,驾着柴车,穿着破衣,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侍奉周天子,只能用桃木弓棘木箭进贡。齐国是天子的舅父,晋、鲁、卫是天子的胞弟,因此楚国未得赏赐而他们都有。现在周朝和这四国都服侍君王,惟命是从,还敢爱惜宝鼎?”
灵王说:“从前我皇伯祖父昆吾,居住在许国的故地,现在郑国贪心,霸占这块田地,我们如果去要回,他肯给我吗?”子革说:“肯给君王啊!周王不敢爱鼎,郑国岂敢爱田?”
灵王说:“从前诸侯都疏远我楚国,害怕晋国,现在我已把陈国、蔡国和不羹两邑的城池,大加修筑,每处都有战车千乘,其中也有你的功劳。诸侯总会怕我了吧?”子革说:“当然怕君王啊!光是这四处地方,已经使诸侯害怕了,何况又有楚国,诸侯岂敢不惧怕君王?”
这时,工尹路进来请示:“君王命令剖开玉圭以装饰斧柄,请问要制成什么样子?”于是灵王进去察看。析父就对子革说:“您在楚国身负众望,今天和君王谈话,竟像是君王的回声,这样下去,国家怎么办?”子革说:“我已磨快了刀刃,只等君王出来,就要挥刀斩断他的妄想。”
灵王出来,继续谈话。刚好左史倚相快步走过。灵王说:“这是一位很好的史官,你要好好看待他。他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啊!”子革说:“臣曾经问过他,从前周穆王放纵他的私心,打算周游天下,让天下到处留下他的车辙马迹。祭公谋父赋了《祈招》之诗劝他回心转意,穆王因此得善终于祗宫。臣曾问他这首诗,他竟不知道。如果问他更久远的事情,他怎么知道呢?”灵王说:“你可知道吗?”子革说:“知道,这首诗说:‘祈招之乐真和平,显我周朝有德音,想见君王风度好,既如美玉又如金。体贴民情惜民力,不求醉饱逞私心。’”
灵王听了,向子革拱手作揖,进入室内。送上饭来不想吃,躺在床上睡不着,折腾了好几天,还是不能克制自己。后来终于招来祸乱,死于非命。
孔子说:“古话说:‘克制自己的欲望,接受礼仪的约束,这就是仁。’说得真好啊!楚灵王果真能克制私欲,怎么会有乾溪之辱呢?”
子产论政宽猛 (左传)
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
子产执政二十年,内政外交都政绩卓著。“宽猛相济”的主张是他首先提出来的,对后世影响很大。他所说的“猛”,实际是为了预防犯罪,重点还是“宽”,所以得到孔子的赞赏。其实,事物本来是错综复杂的,宽与猛都不是绝对的而是互相渗透的,无论立法执法,都应斟酌情理,宽严结合。成都市武侯祠有副对联说:“不审势,即宽严皆误,”是对本文的补充。现代诗人流沙河又改为“不遵宪,即宽严皆误”,更说到点子上了。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①:“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xiǎn)死焉。水懦弱,民狎(xiá)而玩之②,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
【注释】
①子大叔:郑卿。前522年继子产执政。大,同“太”。②狎:轻忽。玩:玩弄。
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huán pū)之泽①。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注释】
①取人:劫掠甚至杀死过路的人。萑苻:泽名,今河南中牟县西北。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①:‘民亦劳止,汔(qì)可小康②,惠此中国,以绥四方③。’施之以宽也。‘毋从(zòng)诡随④,以谨无良,式遏寇虐⑤,惨不畏明⑥。’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⑦,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qiú)⑧,不刚不柔,布政优优⑨,百禄是遒(qiú)’⑩。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注释】
①《诗》:《诗经》。以下引诗见《民劳》及《长发》。②汔:庶几,表示希望。③中国:中原。周的腹心地区。绥:安抚。④从:通“纵”。诡随:盲目追随别人。⑤式:语助词,无义。遏:制止。⑥惨:语助词,明:上天的明命。⑦能:即安抚。迩:近。⑧竞:争竞,急躁。絿:缓,拖沓。⑨优优:宽和。⑩遒:集聚。
【译文】
郑国的子产有病,对子太叔说:“我死后,必由你执政。只有德行高尚的人,才能用宽大的政令使人民服从。其次就是用严猛的政令了。火性猛烈,人们望着就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柔弱,人们亲近而玩弄它,淹死的人就很多。实行宽大的政令很不容易啊。”他病了几个月就死去。
太叔执政,不忍严猛而务行宽大,郑国的强盗就多起来了。他们聚在萑苻泽,抢劫财物。太叔后悔,说:“我早听他老人家的话,就不致如此了。”就发兵去攻打,把这些强盗全部杀死。郑国的强盗才稍稍收敛。
孔子说:“好啊!政令宽大,人民就会怠慢;怠慢便以严猛来纠正。政令严猛,人民就会受到残害,又要用宽大来补救。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治就会平和。《诗》说:‘百姓也够劳苦了,希望稍稍得安康;请施恩惠给中国,和平安定抚四方。’这就是要施行宽政。‘奸头滑脑莫放纵,号令严明整歪风,横行霸道要制止,违法乱纪行不通。”这就是以严猛来纠宽大。‘柔远安近,我王安定,’这就是用和平的政治使国家安定。又说:‘不缓不急,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临头。’这就是政治和谐的顶点了。”
子产死去,孔子听到消息,流着泪说:“他的仁爱精神,真是古人的遗风啊!”
吴许越成 (左传)
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
春秋末年,吴越两国互相攻伐,结为世仇。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千古传诵。本篇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着重记述伍子胥劝阻吴王许越议和。他以古例今,说得非常恳切。无奈吴王骄傲自大,忘乎所以,根本听不进去。伍子胥虽因忠谏而死,但他那“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话,对后人还是深有启发。可参看卷三的《诸稽郢行成于吴》、《申胥谏许越成》两文。
吴王夫差败越于夫椒①,报槜(zuì)李也②。遂入越。越子以甲楯(dùn)五千保于会稽③,使大夫种因吴太宰嚭(pǐ)以行成④。
【注释】
①夫差:吴国国君,吴王阖闾的儿子。夫椒:在今江苏吴县太湖中,即包山。②槜李:吴、越边界地名。今浙江嘉兴县一带。定公十四年,越曾大败吴军于此地。③越子:越王勾践。楯:盾牌。会稽:山名。在今浙江绍兴市。④种:文种,越大夫。太宰:官名。嚭:吴国大臣名,善于逢迎,深得吴王夫差宠信。
吴子将许之。伍员(yún)曰①:“不可。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②。’昔有过(guō)浇,杀斟灌以伐斟鄩(xǔn),灭夏后相③,后缗(mín)方娠(shēn),逃出自窦④,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jì)浇能戒之⑤。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⑥,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lún),有田一成,有众一旅⑦。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zhù)诱豷(yì)。遂灭过、戈⑧,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勾践能亲而务施,施不失人,亲不弃劳。与我同壤,而世为仇雠(chóu)。于是乎克而弗取,将又存之,违天而长寇雠,后虽悔之,不可食已⑨。姬之衰也,日可俟(sì)也⑩。介在蛮夷,而长寇雠,以是求伯○11,必不行矣。”
弗听。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zhǎo)乎!”
【注释】
①伍员:即伍子胥,吴国大夫。②滋:滋长。尽:断根。③过:夏朝国名,今山东掖县北。浇:人名。寒浞的儿子。斟灌:夏时国名,今山东寿光县东北。斟鄩:夏朝国名,今山东潍县西南。夏后相:夏朝第五代王,少康的父亲。后缗:夏后相的妻子。娠:怀孕。窦:孔穴。④有仍:国名,今山东济宁县。后缗是有仍国的女儿,所以逃归娘家。⑤少康:夏后相的遗腹子。牧正:主管畜牧的官。惎:憎恨。戒:警戒。⑥椒:浇的大臣。有虞:姚姓国,今山西永济县。庖正:掌管膳食的官。⑦虞思:虞国的国君。纶:地名,今河南虞城县东南。成:方十里。旅:五百人。⑧女艾:少康臣。谍:暗地察看。季杼:少康的儿子。豷:浇的弟弟。戈:豷的封国。⑨长:助长。不可食:吃不消。⑩姬:吴与周王朝同姓,姬姓国之一。日可俟也:犹言指日可待。俟:等待。○11伯:同“霸”。
【译文】
吴王夫差在夫椒打败越军,报了槜李之仇,趁势攻进越国。越王勾践带领披甲持盾的五千人守住会稽山,并派大夫文种,通过吴国的太宰嚭向吴王求和。吴王打算答应他。
伍员说:“万万不可!臣听说:‘树立品德,必须灌溉辛勤;扫除祸害,必须连根拔尽’。从前过国的浇,杀了斟灌又攻打斟鄩,灭了夏王相。相的妻子后缗方怀孕,从城墙的小洞里逃走,回到有仍,生了少康。少康后来做了有仍的牧正,他对浇恨极了,又能警惕戒备。浇派椒四处搜寻少康,少康逃奔有虞,在那里做了庖正,躲避祸害。虞思两个女儿嫁给他,封他在纶邑,有田一成,不过十里,有众一旅,不过五百。但他能布施德政,开始谋划,收集夏朝的余部,使其专心供职。他派女艾去浇那里刺探消息,派季舒去引诱浇的弟弟豷,终于灭亡过国和戈国,恢复夏禹的功业,祭祀夏的祖先,以配享天帝,维护了夏朝的天命。现在吴国不如过国,越国却大于少康,如果让越国强盛起来,吴国岂不就难办了吗?勾践这个人能够亲近臣民,注重施布恩惠。肯施恩惠,就不失民心;亲近臣民,就不会忽略有功之人。他与我国土地相连,世代有仇,现在我们战胜了他,不但不加以消灭,反而打算保全他,这真是违背天命而助长仇敌,将来后悔也来不及了!姬姓的衰亡,指日可待呀。我国处在蛮夷之间,而又助长仇敌,这样谋霸业,行不通啊!”吴王不听。伍员退下来,对人说:“越国用十年时间聚集财富,再用十年时间教育和训练人民,二十年后,吴国的宫殿怕要变成池沼啊!”
相关内容:
页面执行:62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