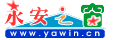
《古文新读—新译新评古文观止》卷五(1)
五帝本纪赞 (司马迁)
本篇及以下十三篇均选自《史记》。《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记载了约三千年历史,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字。全书有五种体裁: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以本纪和列传为主,因此叫做“纪传体”。《二十四史》以《史记》为首,其余各史均沿袭《史记》的体裁,但远不及《史记》的思想卓越,文笔优美。作者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司马谈的儿子,继父职任太史令,公元前99年因为李陵辩护,身受腐刑,后任中书令,忍辱发愤,完成此书。本卷末篇《报任安书》见《汉书》。
五帝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年代久远,传说纷歧。两千年前,司马迁已感到“难言之”。这篇赞语,表现了他的求实精神。文章不满两百字,却曲折回环,寄托了深厚的感情。
太史公曰①:学者多称五帝,尚矣②。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③。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④。余尝西至空峒⑤,北过涿鹿⑥,东渐(jiān)于海⑦,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⑧。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⑨,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jiàn)矣,其轶(yì)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注释】
①太史公:司马迁自称,因其世代担任太史令。《史记》各篇之后多有司马迁的评论,“赞”字是《古文观止》编者加的。②五帝:黄帝、颛顼(zhuān xū)、帝喾(kù)、尧、舜。尚:同“上”,久远。③驯:同“训”。雅训:事有根据,言辞优美。荐绅:同“缙绅”,指士大夫。④宰予:孔子弟子。《宰予问五帝德》、《帝系姓》:见《大戴礼》及《孔子家语》。⑤空峒:山名,又作崆峒,在今甘肃平凉县。⑥涿鹿:山名,在今河北涿鹿县。⑦渐:入,到达。⑧古文:指《尚书》。是:事实,正确。⑨弟:同“第”。顾弟:只是。
【译文】
太史公说:学者们常常说到五帝,五帝的年代太久远了,《尚书》也只记载了尧以来的历史,而诸子百家谈到黄帝,并不严谨可信,有学问的老先生也说不清楚。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和《帝系姓》两篇,儒家多认为不可靠,不相传习。 我曾西到空峒山,北过涿鹿,东临大海,南方泛舟于江淮之上,所到之处,长老们往往指称黄帝、尧、舜的遗迹,风俗教化却各不相同。大概说来,不违背古文记载的,比较近于历史的实际。我发现《春秋》、《国语》对《五帝德》、《帝系姓》的阐述很明显,只是初学者们没有去深入考求,其实它们所表达的并非虚假。《尚书》残缺已久了,而它所遗缺的,往往见于其他的著作。除非好学深思、真有领悟的人,很难向那些见识浅薄、孤陋寡闻的人说清楚。我现在把有关五帝的史料一并论列,选择那记述典雅可信的,写成《五帝本纪》,列为十二本纪的第一篇。
项羽本纪赞 (司马迁)
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当作帝王看待,而在《史记》全书中,《项羽本纪》又是名篇之一,可见他对项羽的态度。赞语既肯定他消灭暴秦的英雄业绩,又叹惜他刚愎自用的转瞬失败。一赞一叹,无限深情。
太史公曰:吾闻之周生曰:“舜目盖重瞳子①”,又闻项羽亦重瞳子②。羽岂其苗裔耶?何兴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jiàng)五诸侯灭秦③,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④,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争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注释】
①周生:汉代儒生。盖,表示揣测。重瞳子:两个瞳仁。②项羽(前232~前202):名籍,字羽,楚贵族。前209年从叔父项梁起兵反秦。钜鹿一战,大败秦军。秦亡,自立为西楚霸王,在五年的楚汉战争中,被刘邦击败,自杀。③将:统率。五诸侯:指齐、赵、韩、魏、燕。当时五国诸侯的后裔,都起兵称王。④义帝:楚怀王之孙,原为牧童,项羽起兵时立为王,尊为义帝。不久又将他放逐杀害。
【译文】
太史公说:我听周生说过,舜的眼睛是双瞳孔,又听说项羽也是双瞳孔,莫非他是舜的后代吧?何以兴起得如此迅猛呢!秦朝虐民失政,陈涉首先发难,天下豪杰纷纷起来,相互竞争,多得数不清。项羽并没有尺寸之地,乘势从田野崛起,仅仅三年,就统率五国诸侯灭亡了秦朝,分裂天下土地,大封王侯,一切政事,全由项羽一人决定,号称“霸王”。虽然未能终久,而近古以来,还没有像他这样的人物!随后他放弃关中而怀恋楚国,失去了地利①;放逐义帝而自立,失尽了人心;却又埋怨诸侯背叛自己,这就太难了!项羽自以为功劳大,骄傲得很,只凭个人的才智,不师法古人,以为只靠武力征伐,就可一统天下,完成霸业,结果五年就亡国,身死东城,还不觉悟,不肯自责,实在错了!临死还说“上天亡我,并非我用兵之罪”,岂不荒谬吗?
①“背关”有另一种理解:“因项羽背弃入关为王之约,已失人心”,见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
秦楚之际月表 (司马迁)
表是《史记》创立的一种体例,或为大事表,或为人物表,便于读者通览全局,大多按年记述。秦汉之际,变化很快,因此按月记述,称为月表。序言概括了这段历史的风云变幻,揭示了秦亡汉兴的原因,以反问作结,颇有馀味。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①;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zuò)②,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shàn)③,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
【注释】
①陈涉:即陈胜,阳城(今河南登封东南)人,农民,秦二世二年(前209年)被征入伍,在蕲县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发动同行戌卒九百人起义,众至数万,被推为王,不久失败。②祚:帝位。③嬗:更替。
昔虞、夏之兴,积善累功数十年,德洽百姓,摄行政事,考之于天,然后在位。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不期而会孟津八百诸侯①,犹以为未可;其后乃放弑②。秦起襄公③,章于文、缪,献、孝之后④,稍以蚕食六国;百有余载,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
【注释】
①孟津:地名,今河南孟津市东,孟县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时曾在此会八百诸侯。②放:指商汤放逐夏桀。弑:指周武王杀商纣。③襄公: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征有功,被平王封为诸侯。④章:同“彰”。缪:同“穆”。文、穆、献、孝:都是秦国的君主。秦穆公始称霸,秦孝公变法富强。
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于是无尺土之封,堕坏名城,销锋镝(dí)①,锄豪杰,维万世之安②。然王迹之兴,起于闾巷,合从(zòng)讨伐③,轶(yì)于三代④,乡秦之禁⑤,适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
【注释】
①锋:刀刃。镝:箭头。②维:希望。③合从:同“合纵”。此处即指联合。④轶:超越。⑤乡:同“向”,以前。
【译文】
太史公读了秦、楚之际的记载,说:最先揭竿起事的是陈涉;以暴力灭秦的是项羽;拨乱诛暴,平定海内,终于登上帝位,完成统一大业的是汉家。五年之间,号令变了三次,自有人类以来,帝王受天命而变更,还未曾有这样急促的。
当初虞舜和夏禹的兴起,积累善事和功劳达数十年之久,恩德普及到百姓身上。他们先是代理王政,又接受了上天的考验,然后才登帝位。商汤和周武的统一天下,则是由契和后稷开始,修仁行义十几代,周武王初次伐纣,未经约定,便有八百诸侯会师孟津,武王还认为时机未熟。后来才杀了商纣。秦朝从襄公兴起,文公、穆公才实力强盛,献公、孝公之后才蚕食六国。经历一百多年,到秦始皇才统一天下。用德治如虞夏商周,用武力如秦,可见统一天下是多么艰巨啊!
秦王称帝之后,考虑到过去所以战祸连绵,是因诸侯并立的缘故。于是不再分封诸侯,并且毁坏名城,销毁民间兵器,铲除各地豪强,自以为可保持万世帝业。结果呢?帝王兴起在闾巷的平民之间,各地豪杰联合讨秦,声势之猛烈远超过三代。以前秦朝的种种禁令,反而帮助贤者排除了种种障碍。那发愤有为而威扬天下的英雄,岂是没有封地便不能称帝称王?这真是古书所说的大圣人啊!难道不是天意吗?难道不是天意吗?如果不是大圣人,谁在这乱世而接受天命登上帝位呢?
高祖功臣侯年表 (司马迁)
刘邦封了一百四十个功臣为侯,年表记载了他们及其后裔的情况,结果大都不妙,到司马迁执笔时,只剩下五位侯爵。汉朝法网固然太密,根本原因还是功臣的子孙因富贵而骄奢淫乱,自投法网。序言于此,反复强调,具有深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①,积日曰阅②。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③。国以永宁,爰及苗裔。”始未尝不欲固其根本,而枝叶稍陵夷衰微也④。
【注释】
①伐:同“阀”,功绩。②阅:经历。③厉:同“砺”,磨刀石。④枝叶:指后世子孙。陵夷:衰落。
余读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异哉所闻!《书》曰“协和万国”,迁于夏、商,或数千岁。盖周封八百,幽、厉之后,见于《春秋》。《尚书》有唐、虞之侯伯,历三代而千有馀载,自全以蕃卫天子①,岂非笃于仁义、奉上法哉?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馀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②,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③,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bì)④。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殒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焉⑤,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
【注释】
①蕃:同“藩”,屏障。②息:滋息,繁育。③萧、曹、绛、灌:指萧何、曹参、周勃、灌婴,都是汉初的大功臣。④嬖:宠爱,也指被宠爱的婢妾。⑤罔:同“网”。
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gǔn)乎①?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见其文,颇有所不尽本末,著其明,疑者阙之。后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览焉。
【注释】
①绲:原意为绳,捆,这里是混合、等同的意思。
【译文】
太史公说:古时人臣的功劳分为五等,用德行辅立宗庙,安定社稷,叫做“勋”;以言论,叫做“劳”;以武力,叫做“功”;按功劳大小分别等级,叫做“伐”;累积资历,叫做“阅”。封爵时的誓词是:“即使黄河变得窄如衣带,泰山变得小如磨刀石①,邦国也永远安宁,传给子子孙孙。”当初何尝不想它根基稳固,可是到了后来,枝叶就渐渐凋零了。
我读了高祖之时功臣封爵的记载,考察当初受封和后来失爵的情况,说:我所闻见的真可惊异啊!《尚书》说:“使万邦和睦”,这些国家从唐尧延续到夏、商两代,有的已经几千年了。周初封国八百,到了幽王、厉王之后,《春秋》上面还有记载。唐、虞时代的侯爵伯爵,经历古代一千多年,还能够保全自己、护卫天子,岂不是由于他们能够实行仁义、奉公守法吗?汉朝兴建以来,功臣受封的有一百多人。天下刚刚平定,大城名都的人口流散死亡,剩下户口不过十分之二三,所以大侯的封邑不过万家,小侯只五六百家而已。以后几代,百姓多返回乡里,户数愈来愈多,萧何、曹参、周勃、灌婴等人的封邑甚至有四万家,小侯封邑的户口也成倍增加,财富跟着增长起来,子孙就骄奢过度,忘记祖先创业的艰难,荒淫乱法。到了武帝太初年间,不过百年,只剩下五个侯爵,其余的都因犯法而丧身亡国了。法网固然也过于严密,但他们也没有谨守法令啊!
处在当今的社会,记取古代的行事,是给自己做个镜子罢了,不必和古代的办法雷同。历代帝王的礼法都有差异,总之以成功为目标,怎么可以强求一致呢?看看他们何以得到尊宠后来又遭废辱,也就可以看清当代得失的道理了,何必定要回顾过去的传闻呢?我于是慎重地考核终始,列表说明,其中也有一些本末不详尽之处,有疑惑的就空下,只把事迹详明的记下来。后来的君子,如果想加以推究,可以参阅。
①另译:“只要黄河像衣带一般没有断缺,泰山像磨刀石一样坚硬而挺立。”见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
孔子世家赞 (司马迁)
《史记》把孔子列入世家 ,与王侯并列,足见司马迁对孔子的崇敬。赞语一唱三叹,表达了无限敬仰之情。
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①。”虽不能至,然心乡(xiàng)往之②。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低回留之③,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⑤,折中于夫子⑥,可谓至圣矣!
【注释】
①止:语助词。高山:比喻道德高尚。景行:大路,比喻光明正大。②乡:同“向”。③低回:徘徊。④布衣:平民。⑤六艺: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⑥折中:亦作“折衷”,作为判断事物的准则。
【译文】
太史公说:《诗经》有这样的话:“仰望巍巍的高山令人崇敬,走上平坦的大道迈步前进。”我虽达不到这种境地,心中总是向往着它。我读了孔子的遗书,更想见他人格的伟大。我到鲁国,看到他的庙堂,以及他用过的车辆、衣服、礼器;学生们还按时在孔子的家庙演习礼仪,使我徘徊留恋,不忍离开。自古以来,天下的君王以至贤士也够多了,他们在世的时候都很荣耀,一死就都完了。孔子只是一个平民,他的学术却传了十几代,学者都尊崇他。自天子王侯以下,在中国凡是讲求六艺的,都以孔子的学说为准则,他真可说是至圣了。
外戚世家序 (司马迁)
《史记》中的外戚,包括后妃本人在内,所以序中提到“夫妇之际”、“妃匹之爱”。外戚是中国历史上一大祸害,此文写得闪闪烁烁,是不是除天命难言而外,还有别的难言之隐呢?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①,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妹喜②;殷之兴也以有娀(sōng),纣之杀也嬖妲(dá)己③;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④。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jū)》⑤,《书》美厘降⑥,《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⑦。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yú)?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⑧,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⑨;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yāo)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⑩,恶(wū)能识乎性命哉?
【注释】
①继体:继位。守文:遵守先帝的法度。②涂山:国名,传说禹娶涂山氏女为妻。妹喜:夏桀之妃,有施氏之女。③有娀:国名。传说帝喾次妃为有娀氏之女。④姜原:周始祖后稷之母。大任:又作太任,周文王之母。禽:同擒。褒姒:周幽王宠妃。⑤乾、坤:《周易》两个卦名,乾为天为阳,坤为地为阴。关雎:《诗经》第一篇。⑥厘:料理。降:下,指尧把二女娥皇、女英嫁给舜。⑦兢兢:小心谨慎。⑧妃:同“配”。妃匹:配偶。⑨子姓:子孙。⑩幽明:指天地间可见和不可见、有形和无形的各种事物。
【译文】
自古以来,承受天命开创基业的帝王,以及继位守成的君主,不仅因他个人内在的品德高,也得到外戚的辅助。夏朝的兴起因娶涂山氏的女儿,而夏桀的流放因宠幸妹喜;殷朝的兴起因娶了有娀氏的女儿,而商纣的兵败自杀因宠幸妲己;周朝的兴起因娶了姜原和大任,而周幽王被擒因他淫乱于褒姒。所以《易》以乾坤两卦为基础,《诗》以《关雎》美后妃之德开端,《尚书•尧典》赞美尧把两个女儿下嫁给舜,《春秋》讥讽娶妻不行亲迎之礼。夫妇之间,存在着人道的大伦啊!所以礼的应用,在婚姻上尤为慎重。音乐和谐能使四时和顺,阴阳的变化是万物生化的根源,能不慎重吗?人能弘扬道义,对命运却无可奈何。尤其那夫妻间的情爱,君主不能自臣子那里得到,父亲不能从儿子那里得到,何况卑贱的人啊①!既已交欢而结合了,或许不能生育;能够生育,结局又不美满:岂不是命运吗?孔子极少谈到命运,大约是很难说得清楚吧。除非是通晓天地幽明的变化,否则又如何能够说明性命的道理呢?
①另译:“甚且,夫妇配偶亲爱的情感,以君主的尊贵,也不能改变臣子的所爱,以父亲的尊严,也不能改易儿子的所爱,何况影响力比君父更卑下的啊。”(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白话史记》)
伯夷列传(司马迁)
本文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伯夷、叔齐的事迹本来不多,而其志行的高洁,遭遇的不幸,却激起太史公的深切同情。因此文章以抒情议论为主,并以许由、务光、颜渊为陪衬,杂引经传,纵横变化,淋漓尽致地抒发了怀疑天道、不满世道的愤懑。前人认为是“列传之变体,文章之绝唱”。
夫学者载籍极博①,犹考信于六艺。《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②。尧将逊位,让于虞舜,舜、禹之间,岳牧咸荐③,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④,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⑤,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及夏之时,有卞随、务光者⑥。此何以称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⑦。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⑧。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⑨,何哉?
【注释】
①载籍:书籍。②虞、夏之文: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等篇。③岳牧:四岳和十二州牧。四岳,传说为尧舜时四方部落的首领。④典职:任职,管理政务。⑤许由:传说尧让帝位给许由,不受,死后葬在箕山,也叫许由山。⑥卞随、务光:传说商汤要征伐夏桀,向他俩先征求意见,都说不知道。后来,商汤又要让帝位于他们,他们拒绝,投水而死。⑦盖:表示疑问。⑧吴太伯:周太王的长子。太王有三子:太伯、仲雍、季历。季历的儿子就是周文王姬昌。周太王预见到姬昌的圣德,有意传位给幼子。太伯即同仲雍出走吴国,故称吴太伯。⑨其文辞:指经传上记载论述的言辞。少:稍微,略为。概:大略。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①。其传曰: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②。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③,“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④:“父死不葬,爰及干戈⑤,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⑥。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⑦。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⑧,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⑨。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⑩?
于(xū)嗟(jiē)徂(cú)兮○11,
命之衰矣!
遂饿死于首阳山。由此观之,怨邪(yé)非邪?
【注释】
①悲:怜悯,同情。睹:观,看。轶:通佚、逸,散失。②孤竹:在今河北省卢龙县。③西伯昌:指周文王姬昌。④叩马:勒住马。⑤爰:就,于是。⑥左右:旁边侍候的人。兵:用作动词,用兵器杀害。⑦太公:武王军师姜太公,名尚,字子牙。⑧宗周:尊奉周王朝为宗主国。⑨首阳山:即下文的西山。今山西省永济县西南。薇:巢菜,又称野豌豆,嫩茎、叶可食。⑩安:哪里。适归:归往。○11于嗟:表悲叹。徂:通“殂”,死亡。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yé)?积仁絜(jié)行如此而饿死①。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②。然回也屡空(kòng),糟糠不厌,而卒早夭③。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zhí)日杀不辜④,肝人之肉⑤,暴戾恣睢(suī)⑥,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⑦,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厚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⑧,时然后出言⑨,行不由径⑩,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11,是邪非邪?
【注释】
①絜:同“洁”,纯洁。②七十子:孔子有三千学生贤人七十。颜渊:即颜回,孔子最得意的门生。③屡空:经常贫困。糟糠:粗糙的食物,即酒糟和糠皮。厌:同餍,吃饱。④跖:古时大盗。⑤肝人之肉:《史记会注考证》说,肝疑为脍之误。脍:切割。⑥暴戾恣睢:残暴凶狠,任意横行。⑦若至:到了。近世:实指当世,作者有所忌讳的借辞。⑧择地而蹈之:选好地方才落步,意为不轻举妄动。⑨时然后出言:该说的时候才说。⑩行不由径:走路不抄小道,办事正大光明。○11:傥:同“倘”。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①。”亦各从其志也。故曰:“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②。”“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③。”举世混浊,清士乃见(xiàn)④。岂以其重若彼,其轻若此哉!
【注释】
①见《论语•卫灵公》。②见《论语•子罕》。执鞭之士,泛指担任卑贱职务,如赶车。③见《论语•子罕》。④见:同“现”,显露。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①。”贾子曰②:“贪夫徇(xùn)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píng)生③。”“同明相照,同类相求④”。 “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⑤。”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⑥。岩穴之士,趋舍有时若此⑦,类名堙(yīn)灭而不称⑧,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⑨,非附青云之士,恶(wū)能施(yì)于后世哉⑩!
【注释】
①见《论语•卫灵公》。疾:忌恨。没世:死了。称:称赞。②贾子:贾谊。引语见其《服鸟赋》。③徇:同“殉”。烈士:志士。夸者,贪权势而矜夸的人。死权:为权而死。众庶:百姓,芸芸众生。冯:同“凭”。④⑤都是引自《易•乾•文言》。⑥附骥尾:比喻依附先辈或名人之后。⑦岩穴之士:指隐士。趋舍有时:出山和退隐,有合适的时机。⑧类:大概。堙灭:埋没。称:称道。⑨闾巷之人:平民百姓。砥行:磨炼德行。⑩青云之士:德行高尚或名位显著的人。施:延续,引申为流传。
【译文】
学者们的典籍虽很广博,仍然要依据六经来考证。《诗》、《书》虽有缺失,关于虞夏两代的记载还是可以看到。尧将退位,让给虞舜。舜后来又让 禹。舜禹都经过四岳九牧的推荐,先代理职务,试行执政,经过几十年的考验,功效非常显著了,才把政权交给他们,可见天下是极贵重的宝器,王位是极重大的法统,传授天下是如此郑重啊!可是有人说,尧曾把帝位让给许由,许由不肯受,还引以为耻,因而逃走隐居。到了夏朝,又有卞随、务光两位隐士。这又该如何解说呢?太史公说:我登过箕山,据说山上有许由的墓。孔子论列古代的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等等,都相当详细。据我所闻,许由、务光的气节都很高尚,可是少见记载,这又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旧仇,因而怨恨很少。”“希求仁德而达到仁德,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对伯夷、叔齐的用心,我很悲伤;看到他们留下来的那篇逸诗,又有点诧异。
他们的传记说: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亲想要叔齐继位。父亲死后,叔齐让位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啊!”于是逃走了。叔齐也不肯继位而逃走了。国人只好立孤竹君的中子为君。这时,伯夷、叔齐听说西伯姬昌仁慈,敬养老人,说:“何不去投奔他呢?”等他们去了,西伯已死。武王用车子载着西伯的灵牌,说是奉文王遗命,向东去讨伐商纣。伯夷、叔齐便拉住马缰,劝阻武王说:“父死不葬,大动干戈,可以说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弑君,可以说是仁吗?”武王的左右要杀他们,太公说:“这是两位义士啊!”便扶他们走开。武王平定了殷朝的祸乱,天下归附周朝,伯夷、叔齐却认为可耻,坚持节义,不食周朝的粮食,隐居首阳山,采摘薇菜充饥。饿得快要死了,还作了一首歌。歌词说:
登上那西山啊,上山采薇。
以暴力代替暴力啊,不以为非!
神农虞夏都已过去啊,何处可归?
眼看就要死去啊,命运衰颓!
于是饿死在首阳山上。这样看来,他们是怨恨,还是并非怨恨呢?
有人说:“上天没有偏心,常常保佑善人。”像伯夷、叔齐,可说是善人了,难道不是吗?这样仁厚,这样高洁,竟然饿死!再说,孔门七十弟子中间,孔子独独称赞颜渊好学,但是颜渊却常贫困,边糟糠也吃不饱, 以致短命。上天对于善人的报答,竟是这样吗?盗跖成天杀害无辜,吃人的心肝,凶狠残暴,聚集党徒几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这又是根据哪门德行呢?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事例啊!到了近代,有的人,操行不合法度,专门违法乱纪,却终身享乐,累世富贵;而有的人谨小慎微,落脚要选地方,说话要看时宜,走路不选小道,非公正的事决不发愤去做,偏偏遭祸惹灾。这类事例真是数也数不清啊。我很怀疑,倘若这就是天道,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孔子说:“如果志向不同,就不用相互磋商。”还是各人依照各人的志向吧!所以孔子又说:“假如富贵可以求得,就是拿着鞭子赶车,我也肯干;假如富贵不可求得,我还是按自己的爱好去做。”“冬天寒冷,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谢的。”正因为整个世界污浊,清高之士才会显现。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把道义看得那么重,才把富贵看得那么轻吗?
“君子痛惜死后而声名不显。”贾子说:“贪夫为财宝而死,烈士为美名而牺牲,野心家为争权而死,老百姓只求安全。”“同是灯火,自然互相照映:同是一类,自然互相呼应。”“云随神龙,风随猛虎,圣人出世,万物都因之显著。”伯夷、叔齐固然贤德,得到孔子的赞誉而声名更加光辉。颜渊固然好学,也因附在千里马的尾巴上才更显著。住在山洞里的隐士,出仕或归隐都能坚持原则,但大多数没没无闻,真是可悲啊。里巷的平民,如果想砥砺德行、建立声誉,但不攀附青云直上之士,怎么能够扬名于后世呢?
相关内容:
页面执行:3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