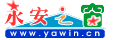
红军在古竹山乡的活动
古竹渡地名自古沿用至今,现有住户60余家。由于地处交通要道,历史以来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第二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也在这里留下了无数战斗的足迹。
村中的“新厝”,堂名“裕德”,本人老家的住宅,咸丰五年(公元1855年)建,为五品副府的宅第,朝廷赐为“武德第”,现乃有四户居住,是磉竹乡、古竹乡人民政府(公元1950——1958年)、洪田人民公社古竹管理区(公元1958——1962年)、古竹人民公社(公元1962——1964年)的机关所在地,1964年公社机关迁到国道205干线边,1968年12月合并入洪田公社。
因为地处交通要道,这个村庄也成为兵匪经常过往和被骚扰的重灾区。每逢有土匪和大兵过境,村中鸡犬不宁,人们都跑到对面河的洋山去避难。三十年代,国民党与红军多次过境甚至驻扎古竹并且交战。游维友、游维灿、游维嵩、游维珍、游维永、游天扬都跑到对面河的洋林盖房子,游维树、游维大到管湾自然村的溪头盖房屋,我的祖父也曾经一度搬到洋林自然村去居住过,游维恭兄弟搬回小磉洋中洋盘大厝祖房,游维兴一家直到解放前夕才回“古竹渡”。经调查,国民党83师,红军101团、红七军团、红九军等部队都在古竹“新厝”和“下坂大厝”(游氏宗祠,占地近十亩,共三进、七重厢房,古时有一百余个房间)两座大房屋驻扎过。本人亲眼见过在“下坂大厝”第二重厢房游维梯的谷仓前的墙壁毛笔竖着书写“一0一团团部”六个字,该厢房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倒闭。当地的老一代人流传着一首红军留下的歌谣:“风吹十九路,豆腐童子兵。风吹十九路,青铁铸红军。”
1933年7月下旬(公历8月)国民党十九路区寿年师在连城被红军击溃北逃,接防永安西路,在洪田、古竹各驻扎一营,古竹一营被红军歼灭,洪田一营溃逃。
开国上将彭绍辉将军在他的1934年日记第24页中记载:八月八日在洪田,八月十三日十一时移苦竹(注:即古竹),十八日离开古竹经马畲(今马洪)到双溪(即磉溪)夜宿。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在古竹住五天的活动。至今,我老家的后堂墙壁上还留着用毛笔字书写的“抗日先遣队十四师政治部”(字迹已消失)、“红军第七师政治部”,墙壁上现存标语,字迹仍然明显的有、“国民党说抗日,为什么十九路士兵来打革命士兵?国民党是投降日本的,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我们要大家共同抗日,必须首先打倒国民党军队”、“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反对国民党出卖中国的卖国主义(行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军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消灭十九路,活捉蒋介石”等。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彭绍辉将军当时任国际少共十四师的师长,从墙壁上所书的“抗日先遣队十四师政治部”文字可以确定该部在我老家驻军。同时,从“抗日先遣队”这几个字可以看出当时红军开始长征的目的已经很明确了。
我少年时,村中老人游维南叙述:“有一年,红军从古竹过船去磉溪,我给他们撑船,到了对面河边,一个军官给我一张红军票。我不要,但是那位军官硬塞给了我。他们走后,我不敢把红军票带回家,用布包好跑到对面山上的长圳灌丛塞着。后来去找,那票没有了。”游维南所指的红军过渡去磉溪,应当就是彭绍辉将军日记所记的那一次。可是,那位红军的军官是何人?老人说不来,不得而知。
邻居叔公游维永(已故)生前多次跟我讲述:大约在1934年3月,红军从连城方向南下经过古竹,跟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国民党卢兴邦部下一个营军队交火。国民党兵有的跑到小磉岭山上,其中一个排的兵退守在我家土楼里,阻击红军。红军围着土楼用迫击炮攻打。有一个国民党的兵头从冬瓜门(靠西那面的圆拱门)探出来看,被红军一枪打中,从门上栽下来。红军继续向小磉岭上国民党卢兴邦发起猛烈的进攻。我家的土堡原来是三层楼房,那一场战斗被红军的炮火轰炸了一层,土堡里的国民党兵大多被烧死;另一部分红军追击那些退守到小磉岭上的国民党军队,从南面追击到大树公,国民党兵逃到小磉水尾的岔路(今小磉村入口处),那个营长被俘虏了,红军获得了大胜。在小磉岭的山上,至今还有当年国民党与红军打仗时留下部分残余的战壕。小磉村的老人回忆,同一天红军在小磉村林氏初一坟与在横仔栋卢兴邦部交战,红军冲锋进攻时在林厝后门山被打死5人。
根据小磉村民回忆:1933年红军101团从我村路过,目的主要是打土豪和富翁,当时群众认识不高看见并来就跑到山上,村庄空无一人。红军往湍石方向去,受到湍石大刀会的阻挡,第三天红军又回头。国民党83师有一个营驻扎在小磉,营长陈增梯,时间一年左右,古历4月撤走。
1934年4月18日,红军攻下永安城,19日乘胜追击国民党残余部队至洪田、古竹,并且狠狠打击了当地的大刀会,大刀会一轰而散。
村中人叙述:1934年8月,红军驻扎在水东村至古竹渡自然村一带,而国民党9师、10师、83师驻扎在大陶洋。国、共两军以大窠村的石辇山和矮岭为界,互相对峙着。当时,红军的指挥部设在水东村的下土堡(清朝康熙年间建,1995年205国道扩建前拆)。一天,有个乞丐来水东村讨饭吃。红军首长在指挥部策划攻打石岭,那乞丐打探到消息连夜便走了。结果,红军去到石岭山时,国民党军队和当地的“大刀会”已经占领了山头。红军一次次组织进攻,遭受了惨重的牺牲代价。当地有两名姓罗“大刀会”的成员,曾经参加过那一次战役,他们分别于2010和2011年才去世。
水东村洋尾的游氏大房屋曾经是朱德等红军居住过的地方,该村从洋头到洋尾的旧民房至今还留下有红军标语,但朱德是否住过没有确切的依据。红军在水东、水西一带驻扎过,这从彭绍辉日记和红军标语可以得到证实。
马洪村和上坪自然村也多次驻扎过红军,留有红军标语,其中有“士兵抗日救国六大纲领”等。
今年6月23日晚,本人到古竹新村采访现年86岁的老人罗永存,他说:“那时我还小,可是知道红军来过好几番,水西洋中的大土楼,还有洪城祠的炮楼子都是那时被烧毁的。我亲眼看见过一次国民党兵从古竹渡上,突然红军从茶林里打出枪来,结果双方打了好久。红军当时可能人不多,最后顺水圳退往水东。”
1935年,国民党修通建、朋公路,83师等部队在古竹只小陶一带沿路戒备森严,其实此时红军已经北上了。
从以上的资料表明,第二次土地革命时期古竹山乡曾经是红军频繁活动的地带。
相关内容:
- 暂无相关内容
栏目热点:
页面执行:14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