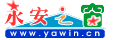
七百年间“邢庄营”
如果说槐南镇安贞堡是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土楼“博物馆”,那么,西洋镇福庄村的“会清堡”俨然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先父”。
福庄,原名“邢庄”,又名“邢庄营”,地处我市南端,西洋镇北部,距市区12公里。因村里人大都姓邢,且均系始祖邢大六公之后裔,故起名为“邢庄”。新中国成立后,“邢庄”被改名为“福庄”。这个居住着200余户人家、800多人口的小山村,四面群山环抱,山溪穿村而过。站在小溪横桥上,看青山如黛,连绵起伏;看沿岸土楼,雄伟古朴。这个平常的自然村落,一度因“会清堡”而扬眉吐气。
◢古朴“邢庄营”
福庄村是一个宋代古村,从南宋宋理宗末年至今已有750多年的历史。
“这个村至今还保存有建于清代的古堡和拥有完整街巷的邢庄营,在传统建筑中至少还有三处留有古代获得功名者留下的石旌表。”今年60多岁的邢氏后裔邢振南介绍,邢庄营又称耸翠山庄,位于福庄村礼朝山下,鹰厦铁路南侧山坡下,有曲尺形的古街巷。邢庄营是邢大六公的开祖基地,内有邢氏宗祠衍庆堂、古戏台、古民居、石旌表等,该建筑群占地1.04万平方米。
邢庄营最有宗亲凝聚力的老厝是衍庆堂,每年农历八月,全国各地的邢姓后裔都要赶赴这里祭祖。据当地流传记忆,邢庄营建于明代,原来的衍庆堂位于现古戏台的位置,后来因为遭受兵匪焚烧,邢庄营在乾隆年间重建时,当时的地理先生认为,将衍庆堂建于现在的位置更容易出官员,因此,衍庆堂便移于现在的位置。修建后的衍庆堂,应验了地理先生的先见,果真出了许多官员。如今,在邢庄营的古戏台前,还有6根高高耸立的石旌表。
衍庆堂的西南侧,为邢庆兴祖厝,祖厝客厅梁枕及其横板有雕花。邢庄营后山是兄弟登科厝,该祖厝也有四根体现古代获得功名者的石旌表,客厅内雕梁画栋,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经典营造法式和精湛的建造技艺,与衍庆堂东南侧和西南侧厢房相似的是,兄弟登科厝的西北侧厢房也有客厅,也是雕梁画栋,同样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经典营造法式和精湛的建造技艺。
在福庄村下头洋的邢元建祖厝门前也有一对石旌表,但因年代久远,该石旌表已经倒塌。据村民介绍,该老厝原建于明代,太平天国年间被焚烧,后于民国年间重建。下头洋还保存了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民主公庙,该庙的大门门口为大花岗岩门槛,外墙有青砖。
“因为邢庄营占地广,加上古街巷七拐八弯,传说,曾经有个乞丐来到村里,三天三夜都走不出村庄。”邢振南介绍,一位去过三坊七巷的人说:“邢庄营没有三坊七巷的面积大,但有比三坊七巷更原始的街巷。”
该村除了现有的古代建筑群外,还保存了古街、古树、古井、古河道等历史环境要素。规模宏伟而又颇具特色的传统建筑,加上完整的历史环境要素,使得福庄村传统村落的特征愈加显现。
◢沧桑“会清堡”
土楼“会清堡”,就坐落在福庄村的右侧。
“福庄现存留的土楼遗址有7处,数‘会清堡’最大。”邢振南说,由于该村的历史相对久远,故文化底蕴十分雄厚,人文景观古朴、典雅,迄今还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古民居建筑群。现保存且有史可考的有会清古堡、书院、民主庙、燕诒堂、羽山公祠、大岚山禁伐碑、富十公祠、衍庆堂、南山拱秀、古戏台、耸翠山庄等。“1956年鹰厦铁路从福庄村经过,将‘邢庄营’一分为二,把耸翠山庄和会清古堡等景点分割在铁路的两边,但整体构造依然存在,前后两部分仍然同在一条线上。”言语中,邢振南略带一丝遗憾。
会清古堡占地面积2500多平方米,背山面水,坐西朝东,取“紫气东来”之喻意。土堡和书斋以及几处邢氏宗祠建筑都十分富有区域特色,屋檐、门窗、梁架、窗棂、斗拱等都有极其精美的雕刻、彩绘、泥塑和壁画图案,具有很高的艺术观赏和建筑科考价值。
会清堡结构为长方形,全部用粘土垒成,墙基用石块砌成,厚达5米,墙高8米余,巍伟壮观。分上下两层,上层南北两面,隔成8间厢房,厢房窗扇雕刻精美,可见当时的工艺水平。环堡有长廊通行,前后各开4个炮窗,临溪一面开11个炮窗,可以眺望远景,也用以防堡匪盗。堡的下层面墙前,建一座堂屋,名燕诒堂。
堂屋前为广坪,种植花木,怡情舒心。堂屋左右侧,开两口水井,不仅供食用,也是防火防匪的重要措施。堡开两个门,南门顶壁上“会清”石匾,楷书端正秀挺,两旁石雕精美,为清代原物。门前原是堡的外院,方圆150平方米,从邢氏族谱上会清堡图所绘,外院有门楼、围墙、便门、厢房小楼和石坪。因年久失修,房子围墙崩塌,只门槛尚在。
出堡北门,进入问渠书院。院名取自宋理学家朱熹的《观书有感》诗名:“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寓意为:读书要探源开好路,循序渐进,在渐进中穷理,达到博学明理的境界。院名不但给子弟做了读书哲理的提示,也为书院增添了浓浓情趣。书院和土堡同时建成,占地200平方米,布局具园林风格,门楼古典雅致,今尚完好。进门回廊曲径,泮池小桥,假山奇石,流水潺潺,花木扶疏,环境幽美。书院左右厢房共6间,供族内子弟读书住宿。粉墙上书画仍清晰可观,洋溢书香气息。
“邢氏有识之士,以会清堡为基地,曾有心发起组织博物苑,致力弘扬民俗文化。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家产’,要开发重修,谈何容易?”今年75岁的邢氏后裔邢锦庚说。
“堡院原来各有一户邢姓农民居住,后来老人去世,子女出外工作,迁居城里,此后,就无人居住了。建国后,土堡除原住户的房间,其余划归公产,作为乡政府的办公处。再后来,村委会迁移堡外新楼办公,土堡无人管理,逐渐荒废。”年事颇高的邢锦庚,看着那些被毁坏的古屋,很是遗憾。老邢说,文革期间,土堡和书院,作为知青住所,带来了欢声笑语。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剧《羊枣之狱》曾在这里拍摄片断,会清堡开始受外界注意。
文化“活化石”
在福庄村《邢氏族谱》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五世孙,名慈观者,以人才选任浙江绍兴府监大使;而丁日以盛至十四孙有沂为邑、诸生文、教敬启,本朝康熙己卯科绍中武榜举人,乾隆庚午科辉运中文榜举人;嗣后,游泮水,贡成均者,相续不绝,以孝友行谊载邑志者,代有其人。”
福庄村人才辈出,历史上出过1名进士,14位举人,贡生64人,秀才无数。
“会清古堡是安贞堡的雏型,时间更久,比安贞堡早建100多年,规模略小于安贞堡,内有三个大赛院,一百多间房。”邢振南介绍,清乾隆30年(公元1766年),侍郎邢婟太(字作屏)退职回乡,他博学多才,深思熟虑,为庇护邻里,给后代留一个安全居处,筹资建筑土堡。古堡规模宏伟,工程浩大,未及竣工,婟太因病逝世。他的三个儿子均有学问和地位,长子邢璋曾官知县,次子邢筠任州县副佐官职,幼子邢丹是举人。他们兄弟3人,遵照父亲遗愿,同心协力,继续建造土堡,清嘉庆年间堡终于建成,历时14年,并取名会清堡。如今,无论是建筑,还是历史,会清堡已俨然是当地文化的一块“活化石”。
与此同时,福庄村内还流传着许多民间故事以及谚语、歌谣等,其中的民间传说《乞丐进邢庄营》《碗人公的传说》《鸭母下金蛋》《梅花落地》和山歌《二十四节气歌》《春米歌》《艄公歌》等堪称民间艺术的精品。村民受历史文化的影响,至今还有邢氏后裔邢崇维等剪纸传人,每逢村民办喜事,都要剪上栩栩如生的剪纸,以图喜庆;每年正月,村民都要舞起龙灯和马灯,喜庆闹节。
一座土楼,一间古厝,一条老街,会清堡犹如一曲凝固的音乐、一段定格的历史,在大山重围的小山村中向世人诉说着邢家人的创业精神和文明生活。
“两年前,我也在这个村里待过几个月,我比你们更早地感觉到了痛心。关于修堡一事,我曾问过一些村民,他们只是说,在那穷乡僻壤之地要重复它的新貌,不是一个小小的数目啊……”随行的驻村干部小罗说。
如今的会清古堡,满目荒凉,破砖碎瓦,杂草丛生,处处蛛网灰空,门窗残败,一片破落景象,沉睡在堡内的每块砖,每根梁柱,彷佛都在诉说百年沧桑!面对如此这般景象,巍伟屹立的会清堡,什么时候才能安抚村民们的“期望”?(童长福魏兴谷陈毅翔文/图)
相关内容:
- 暂无相关内容
栏目热点:
页面执行:31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