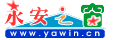
一个探寻永安抗战足迹记者的真情告白
你也许不知道闽江上游有一条不知名的燕江。燕江是闽西北重镇永安绕城的溪河,不只因为她有宽阔的河床,两岸秀丽的风光,来的游客都知道,燕江因是众多燕子自己的家园栖身而得名。
你也许真不知道,当年抗战烽火中的永安戏剧节有多红火;你也许就是不知道,当时永安戏剧节时街头卖出的“戏剧饼”,让小商贩赚了多少小钱?
近年来,在福州,当地的、外来的,想去剧场看一场闽剧,是很难很难的事。人们很难相信,在60多年前的闽西北重镇永安,活跃的戏剧演出活动,给历史留下了浓浓的一笔重墨。
在老永安市委破旧的楼房里,市委党史办的同志热情接待了我这位不速之客。他们为我打开了封尘已久的历史画卷,我似乎看到了当年戏剧工作者一张张和蔼从容、饱含热忱的面孔,看到了鲜为人知的事。抗日战争时期福州沦陷,国民党省政府迁至永安,临时福建省会的永安,逐渐成为我国东南各省的文化中心,各色人等纷纷汇集山城,其中有不少革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支持下,他们创办了许多文艺刊物,仅戏剧方面就有《战时国民教育戏剧丛书》、《福建剧坛》等。当时邵荃麟同志是党在闽浙等地文化方面的领导,他具体委托王西彦同志来永安开辟文艺阵地。宗旨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国民党当局眼见进步刊物如雨后春笋,威胁日甚,不得不施加种种压力。在中共组织的正确引导下,各种进步文艺刊物在创办中风波迭起,经过进步力量的巧妙周旋和较量,终于顶住了逆流,顺利地发行和问世。
永安,燕江绕着燕城,是八闽的腹地,日本鬼子根本就“安达低”,山城竟然接纳了那么多的名流、精英、志士(当然也有不少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们就像南来此飞的燕子在这里筑巢,在这里孕育新的生命。
春风春雨扑面而来,作为抗战文化追梦者的我,久久地伫立在燕江边,很难想象,当今我们党和政府养着众多的文艺工作者,有着相当优厚的待遇、有着非常好的工作条件,出作品还是那么的难,看一场地方戏剧都不容易。当时,是多么艰苦的条件,怎么就创造了奇迹?
其时,永安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当数“戏剧节”。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年二月十五日为“戏剧节”,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以法定的“戏剧节”,来倡导戏剧革新,宣传抗日救国。永安在解放前剧坛最红火的两年,就是1944、1945年的两届“戏剧节”。虽是由国民党福建省党部领导,但具体参与筹办的售货员多是文化界进步人士。时任福建省图书馆馆长的董秋芳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们提出:“戏剧为社会教育,剧人应身体力行”的口号。演出的剧目,不但有名家名作,也有自己创作的剧目。省民众教育馆及时举办了戏剧史料展览会,展览会内容十分丰富,有戏剧理论,戏剧技术、文学剧本、舞台照片等。对当时乃至东南省份戏剧内容与形式的探讨和改进,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剧目除了专业剧团排演的传统剧目外,更多的是话剧,市民称为“便衣剧”,在永安的市民眼中,首次出现了不穿“戏服”,贴近他们生活、贴近他们情感的戏剧。如林谷导演的《青春》、蒋海溶导演的《棋逢对手》、陈新民导演的《正在想》、萧斧编剧、许超然导演的《燕归来》、陈春江江导演的《伶港人家》等。这些剧目有宣传抗日的,还有讽刺和批判当时社会制度的。为了免遭“非议”,他们还安排了一些政治性不强的剧目和“官样”节目穿插演出,展示了我党地下工作高超的斗争艺术。
我特地到了市郊吉山村,因为我省著名的剧作家林舒谦先生、我们闽剧编剧的老前辈,曾经在这里战斗过。他有影响的创作、改编剧目《炼印》、《六离门》等曾轰动省内外剧坛,脍炙人口的《炼印》还拍成了电影,也是闽剧难得的一部能上银幕的艺术片。他1911年生于福州,自大学时起,即组织、参加抗敌救亡话剧团体。“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南京相继失陷;东南沿海亦遭日军铁蹄蹂躏,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938年5月内迁闽西北重镇永安。与戏剧结缘的林舒谦,此时便到永安任伪省府教育厅戏剧委员会“战时国民巡回教育团”干事。当时的教育厅在市郊吉山,永安城里有个办事处,施教团是在城里。1939年教育部派来了教育二队,队长谷剑尘。省教育厅计划办话剧队,招生20多人交教育部二队训练三个月,毕业后由陈启肃带队。因此,省教育厅又于1939年9月16日成立“战时国民教育巡回教育团”,陈启肃为团长,林舒谦、许栖萍为干事,下分三个股,陈启肃兼总务,林舒谦兼教导,许栖萍兼演出股,林舒谦作为骨干分子,起到了挑大梁的作用,该团演出的《三叉口》、《菱姑》、《战》等剧目,都系林舒谦、陈启肃创作的三幕剧。
在此同时,临时省会永安有过“特种巡回教育团”,在国民党福建省党部的操纵下,专门演出一些内容极为反动的剧(节)目,为国民党歌功颂德,宣称“闽系老区被毒化,必须消毒”。其时的林舒谦、陈启肃等与中共地下党员卢茅居保持着密切联系。卢茅居当时住在虾蛤村,公开身份是《现代青年》杂志的主编,一般每月来找林舒谦两次,一次组稿,一次取稿。林舒谦在积极为进步书刊写稿的同时,无形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针对“特种巡回教育团”的演出宣传,施教团创作、演出了许多宣传抗战的进步剧目,发挥了戏剧团体的特殊作用。后“战教团”改为“民众教育施教团”,分设一、二、三团,林舒谦任第一团团长。他所在的施教团以戏剧演出为主,每月在永安公演一次,巡回于闽西北的大田、尤溪等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演出剧目有《县长太太》、《最后一幕》、《泾渭》、《仇》、《同一线上》、《黑箱》、《自投罗网》、《岭上梅》、《为国牺牲》、《徘徊的女人》、《好汉子》、《喷火口》、《落日》、《毒》、《生死线》等。1940年,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创办《剧教》月刊,林舒谦任主编,相继创作、发表了《喷火口》、《毒》等一批戏剧作品,尤其在永安举办的两届“戏剧节”中,林舒谦、陈启肃、许栖萍、董秋芳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戏剧为武器,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奋起抗争,占领了闽西北政治文化阵地,为抗战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吉山村,再也找不到当年小山村的感觉,其实如今早已成了城区一隅,哪儿还有老前辈曾经战斗过的教育厅遗址、遗迹?只有吉山老酒还是老味道,吉山土鸡闻了名。
我又慕名寻找永安大戏院,这里已夷为平地,正在建筑一座新的高楼。这里的朋友告诉我,永安到改革开放时期一直保留着三个影剧院,到现在,永安已没了一个演戏的地方。再一打听,永安在1985年京剧团撤消后,早就没了剧团。没了剧团,还要什么影剧院干嘛?
真难以想象,那时,那时的戏剧怎么就那么样的盛况空前?
据记载:“戏剧节”演出地点在永安大戏院,共演出了十多天。“戏剧节”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支持,永安各报副刊连日发表了有关“戏剧节”的评论和花絮。有趣的是,演出期间,台上演新潮戏,街头还义卖设计有希腊羊神脸谱的“戏剧饼”。市井人头撵动,大家争先品尝新奇的“戏剧饼”,商贩居然一夜身价百倍,“戏剧饼”供不应求,一时名噪燕城。
问你也“安达低”,“戏剧饼”都供不应求,那么观众究竟有多少?在十几年搞戏曲志调研的时候,吃过“戏剧饼”的一位老爷子对我们说,省城来的,省外来的,乡下来的,“安达低”有多少人凑热闹,那场面大着呐。
可以想象,那时没有电影、电视,就连广播也是希罕的玩意儿,戏剧就是市民、村民的文化大餐。正是这些文化大餐,不仅在当地播下对日本鬼子仇恨的种子,助燃了他们心中的抗日烽火,让南来北飞的燕子,将信息传递到大江南北……
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无法统计,当年上演的《青春》、《为国牺牲》、《燕归来》等剧目有多少流传到内地的舞台,又有多少热血男儿在《棋逢对手》、《好汉子》、《生死线》这些剧目的感召下走上了抗日战场,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往事,不会随着燕江的水,静静地流逝。
尽管,那些上演的剧目,都不是什么经典力作,甚至有些是应景的戏文,甚至在当今一些大剧作家眼里是概念化的作品,根本无法与福建省近年推出的全国十大精品戏剧《贬官记》、《董生与李氏》等相媲美,不仅没有那么厚重,难以流传后世,甚至有的是昙花一现,但就是那一现的昙花,也是那么的赏心悦目,乃至震撼人心,给当时当地的观众起到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推动历史的作用。
也许你们还“安达低”,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在永安青水畲族乡发现了戏剧艺术的活化石——“大腔戏”。大腔戏约于明代中叶宣告消亡,《辞海》中只注明:“大腔戏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经国内专家多方论证,结论确为“大腔戏”,这一惊人的发现,为中华文明史填补了重要一笔。而永安的抗战戏剧文学,也同“大腔戏”一样,给后人留下不尽的文化库存。
前不久,笔者为国家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项目,再度走访永安,想再找当年目睹过“戏剧节”的观众,已很寻找到知情老人了。毕竟过去了六十多年,这时间的跨度太长了点,见证历史的人大都相继离开了我们……
不过,滔滔东去的燕江水,永远流失不了她的记忆。即使过了百年、千年,河水淘去再多淤泥残沙,也淘不走历史的积淀。
两届特殊环境、特定时期永安的“戏剧节”,是我党领导下的进步文化人士以戏剧为武器,既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同时又起到了普及戏剧艺术、创新戏剧艺术、提高戏剧艺术的作用。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不能不说是我省戏剧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
六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燕城面貌焕然一新,遗址大都被崭新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但燕城依然口口相传着抗战文化人士诸多感人的传说。因为,历史不会忘记,燕江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永安城虽然在抗战时期没有对着日本鬼子放过一枪一炮,我想,她发挥的作用,不小于枪炮的威力。
页面执行:15ms